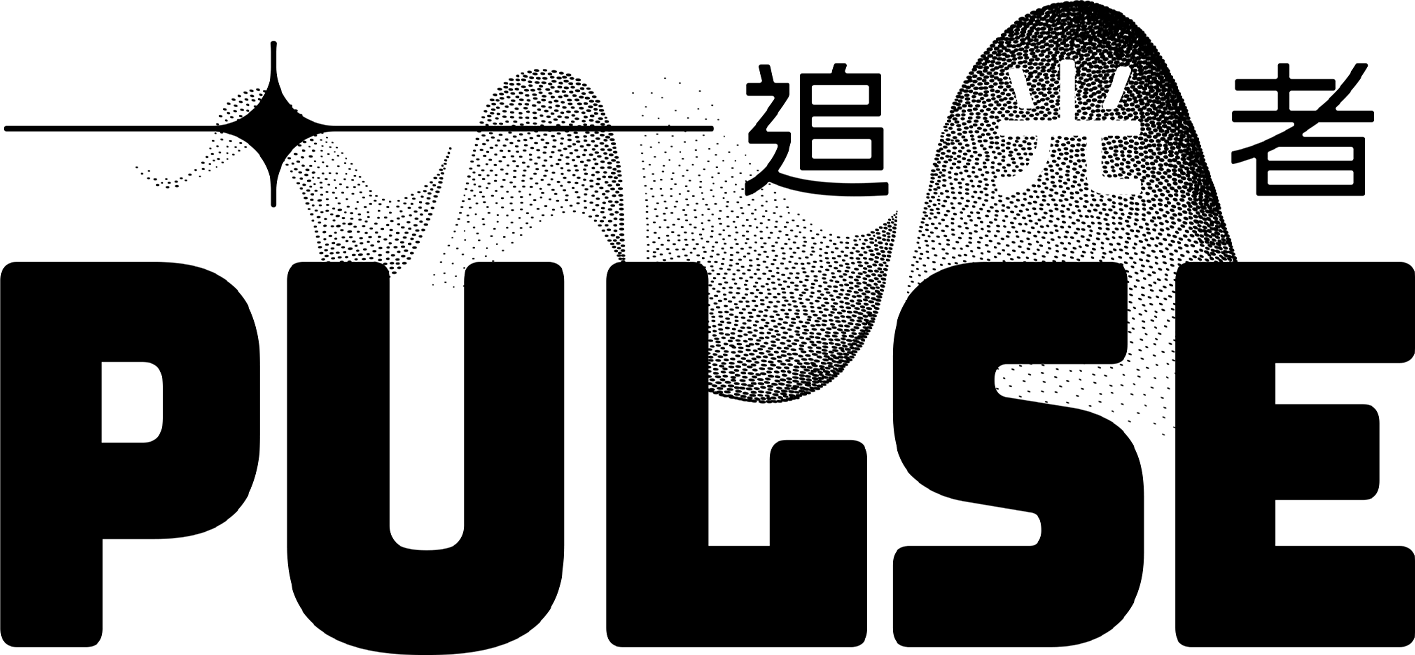一、震撼與疑惑
月前造訪廣島與長崎,參觀兩處的原爆資料館、和平紀念公園及相關遺跡,心中感慨萬千。原爆資料館內陳列的照片確實震撼人心:燒焦的衣物、停止的時鐘、融化的玻璃瓶、輻射灼傷的皮膚標本、兒童的遺物。那些被原子彈瞬間氣化的人影烙印在石階上,成為人類歷史上最駭人的剪影。1945年8月6日和9日,兩顆原子彈分別投落廣島與長崎,造成超過二十萬人直接死亡,此後數十年間因輻射後遺症而死者更難以計數。作為人類史上唯一遭受核武攻擊的國家,日本人的受害者身份似乎無可爭議。
然而,在震撼與悲憫之餘,一種隱隱的不安逐漸浮現。兩座資料館皆詳述原爆經過、核武器的恐怖威力、受害者的慘況、倖存者(被爆者)的苦難人生,乃至戰後和平運動的發展。這些敘事本身並無不妥,甚至可說是必要的歷史見證。但問題在於:整個展覽對於導致原爆的歷史脈絡——日本何以發動侵略戰爭、何以與美國兵戎相見、何以走到招致如此毀滅性報復的境地——幾乎付之闕如。參觀者若不具備相關歷史知識,極易形成一種印象:日本是一個無辜的受害國,原子彈是從天而降的災難,與日本自身的所作所為毫無關聯。
這種敘事策略——或可稱為選擇性記憶——引發了我對日本戰後歷史觀的深層思考。本文嘗試從原爆敘事出發,探討日本社會如何處理二戰歷史,分析其中的缺失與問題,並與德國的戰後反省進行比較,最後反思完整歷史記憶對於真正和平的意義。
二、原爆的歷史脈絡:被遮蔽的前因
要理解原子彈為何投落日本,必須回溯到更早的歷史。1931年9月,日本關東軍製造柳條湖事件,以此為藉口發動侵略,迅速佔領中國東北全境,扶植偽滿洲國傀儡政權。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此後八年間,日軍在中國大地上犯下無數暴行:南京大屠殺中三十萬以上平民與戰俘遇害;七三一部隊以活人進行細菌戰與人體實驗;重慶大轟炸持續五年餘,造成萬餘平民死傷;三光政策(燒光、殺光、搶光)使華北農村化為焦土。
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將戰火延燒至太平洋。此後三年多,日軍橫掃東南亞與太平洋諸島,建立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在這個過程中,日軍對佔領區人民施以殘酷統治:菲律賓巴丹死亡行軍中,七萬餘美菲戰俘在酷刑、飢餓與疾病下死亡過半;緬甸鐵路(死亡鐵路)建設中,逾十萬亞洲勞工與萬餘盟軍戰俘喪生;慰安婦制度強迫數十萬亞洲女性為日軍提供性服務;新加坡肅清大屠殺中數萬華人遭殺害。整個亞太戰爭期間,日本侵略導致的死亡人數估計在一千五百萬至二千萬之間,其中絕大多數是平民。
正是在這一歷史脈絡下,美國決定對日本使用原子彈。這一決定本身當然可以從多個角度進行批判:核武器的無差別殺傷性質、對平民目標的攻擊、是否存在替代方案(如封鎖、常規轟炸、有條件投降談判等)、是否意在向蘇聯展示實力等。這些都是重要的歷史與倫理問題,值得深入探討。然而,若要全面理解原爆事件,就不能將其與日本的侵略戰爭割裂開來。原爆是戰爭的產物,而日本正是這場戰爭的發動者。受害者敘事若不伴隨加害者反省,便是殘缺的歷史。
廣島與長崎的原爆資料館對上述歷史脈絡著墨甚少。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在2019年完成翻新後,確實增加了一些關於戰爭背景的展示,但這些內容被置於邊緣位置,篇幅有限,語調模糊。例如,對於日本的軍事擴張,展覽使用的措辭往往是「進出」而非「侵略」,這種語言選擇本身就反映了一種迴避態度。
三、長崎原爆資料館的「加害展示」論爭
然而,日本社會對於原爆敘事的態度並非鐵板一塊。長崎原爆資料館在1996年重建開館前後引發的「加害展示」論爭,正揭示了日本內部圍繞戰爭記憶的激烈角力。
1992年,長崎市為紀念原子彈爆炸五十週年,著手重建長崎國際文化會館(後更名為長崎原爆資料館)。時任市長本島等在籌備過程中明確表態:展覽內容必須基於日本侵略歷史的認識。本島並非一般的地方官員。1988年,他曾在長崎市議會公開主張天皇應承擔戰爭責任,此言一出,立即遭到天皇主義者與右翼團體的持續威脅。1990年1月,本島更遭右翼團體幹部槍擊,身受重傷,住院療養一個月之久。
正是這位九死一生的市長,堅持在長崎原爆資料館中加入「加害展示」——即展出日本在戰爭中對亞洲各國人民施加暴行的照片與資料,包括慰安婦問題、七三一部隊細菌戰、南京大屠殺等。本島的信念是:唯有承認日本的加害者身份,才能向亞洲各國民眾傳遞「可共享的歷史觀」,原爆的悲劇才能獲得真正的理解與同情。
然而,這一嘗試從一開始就阻力重重。本島深知,若將加害展示的具體內容提交市議會公開審議,「根本不可能達成共識」。因此,整個展覽籌備過程採取秘密進行的方式,具體展品內容直至開館前夕仍完全保密。1995年,繼承本島路線的伊藤一長就任市長,繼續推動加害展示的實現。
1996年1月,《朝日新聞》公開報導加害展示計畫,保守派議員與右翼團體隨即施加強大壓力,要求撤除相關照片。在開館前夕,長崎市政府一度決定替換「加害照片」。此舉立即引發中國《人民日報》的批評,指責「資料館屈服於壓力」;長崎當地華僑亦表達強烈不滿。在內外壓力下,市政府隨即宣布恢復展示加害照片。地方報紙對這番反覆無常提出嚴厲批判,《西日本新聞》以「對中方『顧慮』 臨時抱佛腳的應對 損及信賴」為題,《長崎新聞》則批評這是「缺乏理念的秘密主義必然結果」。
風波並未就此平息。1996年4月資料館開幕後,《產經新聞》揭露館內影像檔案中收錄的南京事件照片,實為法蘭克·卡普拉導演的電影《中國戰場》(1944年)中的重現場景,並非真實歷史影像。這一事件為右翼勢力提供了攻擊加害展示的口實,使整個加害展示計畫的公信力大受打擊。
長崎原爆資料館的加害展示論爭,是理解日本戰後歷史記憶的重要窗口。它表明,日本社會並非沒有反省的聲音。本島等這樣的政治人物,冒著生命危險堅持將加害者意識納入原爆敘事,代表了日本社會中一股可貴的自省力量。然而,這股力量始終處於邊緣,難以撼動主流的受害者敘事。右翼團體的暴力威脅、保守派政客的政治施壓、媒體的選擇性報導,共同構成了壓制反省聲音的強大機制。本島被槍擊而未死,加害展示在重重阻力下勉強保留,但這些「勝利」的代價之高,恰恰說明了日本社會歷史反省之艱難。
四、受害者意識的建構與固化
日本社會的受害者意識並非原爆資料館的獨特現象,而是戰後日本國民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這種記憶的形成有其複雜的歷史原因。
首先是美國佔領時期(1945至1952年)的影響。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HQ)在佔領初期確實推動了非軍事化與民主化改革,包括東京審判對戰爭罪犯的審判。然而,隨著冷戰格局的形成,美國的對日政策發生逆轉。為了將日本納入反共陣營,美國開始淡化日本的戰爭責任,赦免或減刑多名戰犯(包括被指控參與細菌戰的七三一部隊成員),並允許戰前精英重返政壇。天皇裕仁本人雖被東京審判排除在外,得以保留皇位,但這一決定本身就意味著戰爭責任追究的不徹底。
其次是戰後日本政治結構的特殊性。自民黨自1955年成立以來長期執政,黨內保守派勢力與戰前精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岸信介(安倍晉三的外祖父)曾任東條英機內閣的商工大臣,戰後被列為甲級戰犯嫌疑人,卻未受審判,後來更當選首相。這種政治延續性使得對戰爭的徹底反省難以在官方層面展開。
第三是原爆經驗的特殊性。廣島與長崎的慘劇確實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核災難,其恐怖程度與受害者的苦難真實而深切。這種經驗的強烈性使日本社會傾向於聚焦於自身的受害,而較少反思導致這一結果的因果鏈條。「被爆者」成為一個神聖化的身份,其敘事具有道德權威,難以在公共領域中被質疑或置於更廣闊的歷史脈絡中討論。
第四是和平主義與反核運動的興起。戰後日本憲法第九條宣布放棄戰爭與武力,日本社會形成了強烈的和平主義傳統。廣島與長崎成為反核運動的象徵,「無核三原則」(不製造、不擁有、不引進核武器)成為國策。然而,這種和平主義往往以受害者身份為基礎,強調日本是核武器的唯一受害國,而較少追問日本何以成為核攻擊的對象。和平的呼籲與歷史的反省本應相輔相成,但在日本的語境中,前者有時反而成為迴避後者的理由。

五、歷史教育中的缺失與爭議
日本的歷史教育長期以來是國內外爭議的焦點。文部科學省對教科書的審定制度賦予政府相當大的影響力,而這種影響往往傾向於淡化或美化日本的戰爭歷史。
教科書審定中的幾個著名案例可以說明問題。1982年,日本政府要求教科書將「侵略」改為「進出」,引發中國與韓國的強烈抗議,最終導致「近鄰條款」的出台,要求在涉及亞洲鄰國的近現代史記述時考慮國際諒解與協調。然而,這一條款的實際約束力有限。2001年,「新歷史教科書編纂會」編寫的教科書獲准出版,該書大幅淡化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等問題,將日本的戰爭行為描述為「解放亞洲」的行動。雖然這本教科書的實際採用率很低,但其獲准出版本身就反映了政府的態度。
近年來的趨勢更令人憂慮。安倍晉三政府期間(2012至2020年),教科書審定標準進一步收緊。慰安婦問題的相關記述在多種教科書中被刪除或弱化。2021年,日本政府正式決定不再使用「從軍慰安婦」一詞,改用「慰安婦」,理由是前者可能造成「強制連行」的誤解——儘管大量歷史證據表明強制性確實存在。
相比之下,日本民間社會對歷史問題的態度更為多元。部分歷史學者、記者與社會運動者長期致力於揭示歷史真相、推動與鄰國的和解。「家永教科書訴訟」(1965至1997年)是一個標誌性案例:歷史學家家永三郎三次起訴政府,挑戰教科書審定制度,這場長達三十二年的法律鬥爭彰顯了日本社會內部對歷史問題的分歧與抗爭。然而,民間的反省聲音往往難以撼動官方敘事的主導地位。政治家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屢禁不止;每逢8月15日「終戰紀念日」,官方儀式的措辭總是強調日本的戰爭死難者,而非日本造成的他國死難者。
六、遊就館:歷史修正主義的殿堂

去年我曾造訪東京靖國神社,參觀其境內的遊就館。這座軍事博物館的展覽內容,可以說是日本官方歷史敘事最極端的體現,其中對二戰的詮釋令人瞠目。
遊就館的歷史可追溯至1882年,是日本最古老的軍事博物館之一。館名取自《荀子》「遊必就士」之語,原意為「交遊必須結交賢士」。然而,這座以儒學經典命名的博物館,其展覽內容卻與反省、修身的儒學精神背道而馳。戰後遊就館曾一度關閉,1985年重新開放後,逐漸成為日本右翼歷史觀的展示中心。
館內關於二戰的敘事,與廣島長崎原爆資料館的「受害者敘事」有所不同,但同樣迴避了日本的侵略責任。展覽將太平洋戰爭的起因歸結為經濟問題,尤其強調所謂「ABCD包圍網」——即美國、英國、中國、荷蘭對日本實施的經濟封鎖。根據這一敘事,1941年美國凍結日本資產、對日禁運石油,是逼迫日本走上戰爭之路的直接原因。日本偷襲珍珠港因此被描述為一場「被迫的自衛戰爭」,而非蓄謀已久的侵略行動。
這種敘事手法極具誤導性。它將因果關係倒置,隻字不提美國對日本實施經濟制裁的原因——正是因為日本自1931年以來持續侵略中國、1940年進佔法屬印度支那、威脅東南亞,美國才逐步收緊對日制裁。將這些制裁措施描述為無端的「包圍」,而不交代日本在此之前長達十年的侵略擴張,是典型的選擇性敘事。
更令人不安的是遊就館對戰爭本身的美化。展覽將「大東亞戰爭」框架為一場「解放亞洲」的聖戰,聲稱日本是為了將亞洲人民從西方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而戰。館內陳列著神風特攻隊員的遺書、照片與遺物,這些年輕士兵被呈現為純潔的愛國者與悲劇英雄,其「為國捐軀」的精神被無限昇華。至於日軍在亞洲各地犯下的暴行,南京大屠殺、慰安婦制度、戰俘虐待、強制勞動,在遊就館的敘事中幾乎完全缺席。
關於原子彈,遊就館的處理方式同樣耐人尋味。展覽確實提及廣島與長崎遭受核攻擊,但僅以簡短篇幅帶過,將其定性為「日本人的悲劇」。這種處理方式與原爆資料館的詳盡呈現形成對比,卻服務於相同的敘事目的:強調日本的受害者身份,而迴避導致這一結果的歷史脈絡。
遊就館的敘事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它是一座博物館的展覽內容,更因為它與靖國神社的象徵意義緊密相連。靖國神社供奉著約二百四十六萬名戰歿者,其中包括1978年秘密合祀的十四名甲級戰犯——東條英機、廣田弘毅、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日本首相與政治人物參拜靖國神社,客觀上構成對戰爭罪犯的致敬,以及對遊就館所代表的歷史觀的背書。
從長崎原爆資料館的加害展示到東京的遊就館,我們可以看到日本歷史敘事的兩個極端。前者代表了日本社會中試圖正視歷史的微弱努力,卻遭到右翼勢力的強力打壓;後者則是歷史修正主義的集大成之作,將侵略美化為解放,將戰犯塑造為英烈。兩者的對照,恰恰說明了日本社會在歷史記憶問題上的深刻撕裂。
七、比較視角:德國的戰後反省
若要評價日本的歷史處理方式,德國的例子是一個不可迴避的參照。同樣是二戰的戰敗國與加害國,德國對納粹罪行的反省被普遍認為遠比日本徹底。
德國的反省首先體現在法律與制度層面。戰後德國不僅接受了紐倫堡審判對主要戰犯的追訴,更在此後數十年間持續進行「去納粹化」工作。否認大屠殺在德國是刑事犯罪;納粹符號的公開展示被法律禁止;戰爭罪行沒有追訴時效。相比之下,日本雖然經歷了東京審判,但戰後的「逆流」使許多戰犯得以逃脫追訴或重返社會,戰爭責任的法律追究遠不如德國徹底。
德國的反省也體現在政治領導人的公開表態上。1970年,時任西德總理維利·布蘭特在華沙猶太人隔離區起義紀念碑前下跪,這一「華沙之跪」成為德國認罪與和解的標誌性時刻。此後歷屆德國政府均明確承認納粹罪行,向受害者道歉並支付賠償。相比之下,日本政府對慰安婦等問題的態度反覆,每當首相或官員發表道歉聲明,往往很快被其他官員的否認言論所抵消。1993年的「河野談話」承認軍方介入慰安婦招募,但此後政府立場多次動搖,令受害者及其支持者深感受辱。
德國的歷史教育同樣與日本形成鮮明對比。在德國,納粹歷史是必修內容,學生被要求參觀集中營遺址。柏林市中心的「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佔地廣大,時刻提醒人們銘記歷史。德國的博物館與紀念設施不僅呈現受害者的苦難,也詳細展示加害的機制,這種追問直指集體責任的核心。
當然,德國的反省也並非完美無缺。東德時期的反法西斯敘事往往將納粹歸咎於資本主義,從而為東德社會開脫;統一後的德國仍面臨新納粹主義與排外暴力的挑戰。但總體而言,德國社會已形成一種共識:對歷史罪行的承認與反思是國家認同的基礎,也是與鄰國和解的前提。這種共識在日本社會遠未形成。
八、結構性比較:為何日德走向不同?
日德在歷史反省上的差異可以從多個結構性因素加以解釋。首先是戰後國際環境的不同。德國處於歐洲冷戰前線,與法國、波蘭等鄰國的和解是歐洲一體化進程的必要條件。相比之下,亞洲缺乏類似的區域整合機制,美日同盟的存在使美國對日本的歷史問題採取寬容態度。
其次是受害者群體的差異。大屠殺的受害者——猶太人——在戰後建立了以色列國,並在歐美社會擁有相當的政治影響力,能夠持續施壓德國正視歷史。日本侵略的主要受害者——中國、韓國、東南亞國家——在戰後初期國際話語權有限,難以對日本形成有效的歷史問責壓力。
第三是戰爭性質的不同敘事框架。納粹德國的罪行以大屠殺為中心,其種族滅絕的性質使之被普遍視為絕對的道德惡行。相比之下,日本的戰爭被保守派重新框架為「大東亞戰爭」——一場將亞洲從西方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的戰爭,這為迴避反省提供了空間。
第四是天皇制的延續。裕仁天皇在戰後未被追究責任,繼續擔任國家象徵直至1989年去世。納粹政權被完全清算,希特勒自殺身亡,第三帝國土崩瓦解;而日本則保留了天皇制這一象徵性連續體,使「戰前」與「戰後」之間的界線更為模糊。
九、原爆敘事的道德複雜性
回到廣島與長崎的原爆敘事,我們需要承認這一問題的道德複雜性。
一方面,原子彈對平民的大規模殺傷確實構成嚴重的道德問題。無論日本在戰爭中犯下何種罪行,廣島與長崎的普通市民並非戰爭決策者,卻承受了核武器的全部恐怖。從國際人道法的角度看,對平民目標的無差別攻擊本身就是戰爭罪行。美國使用原子彈的決定,無論出於何種戰略考量,都無法完全擺脫道德責難。
尤須指出的是,原爆受害者之中有相當數量並非日本人。據估計,廣島原爆中約有二萬至三萬名朝鮮人罹難,長崎亦有數千名朝鮮人死於核爆。這些朝鮮人絕大多數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被強制徵用的勞工,被迫離鄉背井到日本從事軍需工業與礦山勞動。他們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受害者,卻又在戰爭末期成為原子彈的受害者——雙重的受害,卻長期被日本的原爆敘事所忽視。此外,廣島與長崎還有中國勞工、東南亞戰俘、甚至少數盟軍戰俘在原爆中喪生。這些非日本人的受害者,是真正純粹的受害者:他們與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毫無關係,卻因日本的戰爭而被帶到這片土地,最終葬身於核火之中。長期以來,在日朝鮮人被爆者在申請「被爆者健康手冊」與相關補償時遭遇重重障礙,其苦難未能獲得與日本被爆者同等的承認。這種差別對待,恰恰暴露了日本受害者敘事的選擇性與局限性。
另一方面,原爆敘事若僅止於受害,而不追問何以至此,就會陷入一種道德的自我封閉。歷史不是孤立事件的堆砌,而是因果相連的鏈條。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拒絕投降,是原爆發生的直接前提。將原爆呈現為一場從天而降的災難,而非戰爭邏輯的極端產物,不僅是對歷史的扭曲,也是對和平教育目標的背離。真正的和平不僅意味著反對核武器,更意味著反對導致戰爭的侵略行為。
這種複雜性要求一種更為全面的敘事。原爆資料館完全可以在保持對受害者同情的同時,清晰呈現戰爭的來龍去脈。長崎原爆資料館在本島等市長任內嘗試的「加害展示」,正是這種整合敘事的可貴嘗試。遺憾的是,這一嘗試遭遇了強大的政治阻力,最終只能以妥協的形式保留下來,而整體的敘事框架並未根本改變。
十、結語:完整記憶的必要
廣島與長崎的原爆遺跡,是人類應當永遠銘記的歷史見證。核武器的恐怖、戰爭對平民的殘害、倖存者終生的苦難——這些都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值得後人憑弔與反思。但僅有這些還不夠。
完整的歷史記憶要求我們追問:這場災難是如何發生的?誰發動了戰爭?誰在戰爭中犯下了罪行?受害者不僅在廣島與長崎,也在南京、馬尼拉、新加坡、緬甸鐵路沿線、慰安所的帳篷內、七三一部隊的實驗室中。和平的呼籲若不伴隨對侵略的反省,就會流於空洞;受害者敘事若不與加害者意識並存,就會淪為選擇性記憶。
離開長崎原爆資料館時,我想起了本島等市長的遭遇:一個敢於主張天皇應承擔戰爭責任、堅持在原爆敘事中加入加害展示的政治家,最終被右翼分子的子彈射中。他僥倖生還,但他所代表的歷史反省聲音,在日本社會始終處於邊緣。米蘭•昆德拉曾說:「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對歷史的真正銘記,不僅是為了哀悼死者,更是為了向他們——所有的他們,包括那些在原爆中喪生的朝鮮勞工與中國人——尋求一種遲來的正義。
日本人當然有權紀念原爆受害者,正如任何民族都有權紀念自己的苦難。但真正的和平教育,要求一種更為誠實的歷史態度:承認日本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承認原爆的恐怖源於戰爭的恐怖,而日本正是這場戰爭的發動者。唯有如此,廣島與長崎的教訓才能真正成為人類共同的遺產,而非一個國家自我憐憫的工具。
唯有如此,和平才有可能。
張燦輝
流亡哲學人
《橫流集》專欄系列之前其他文章,請到《追新聞》網站瀏覽:https://thechasernews.co.uk/t/橫流集/
相關新聞
- 2025 年 12 月 20
- 2025 年 12 月 25
- 2025 年 12 月 26
- 2026 年 01 月 29
- 2026 年 01 月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