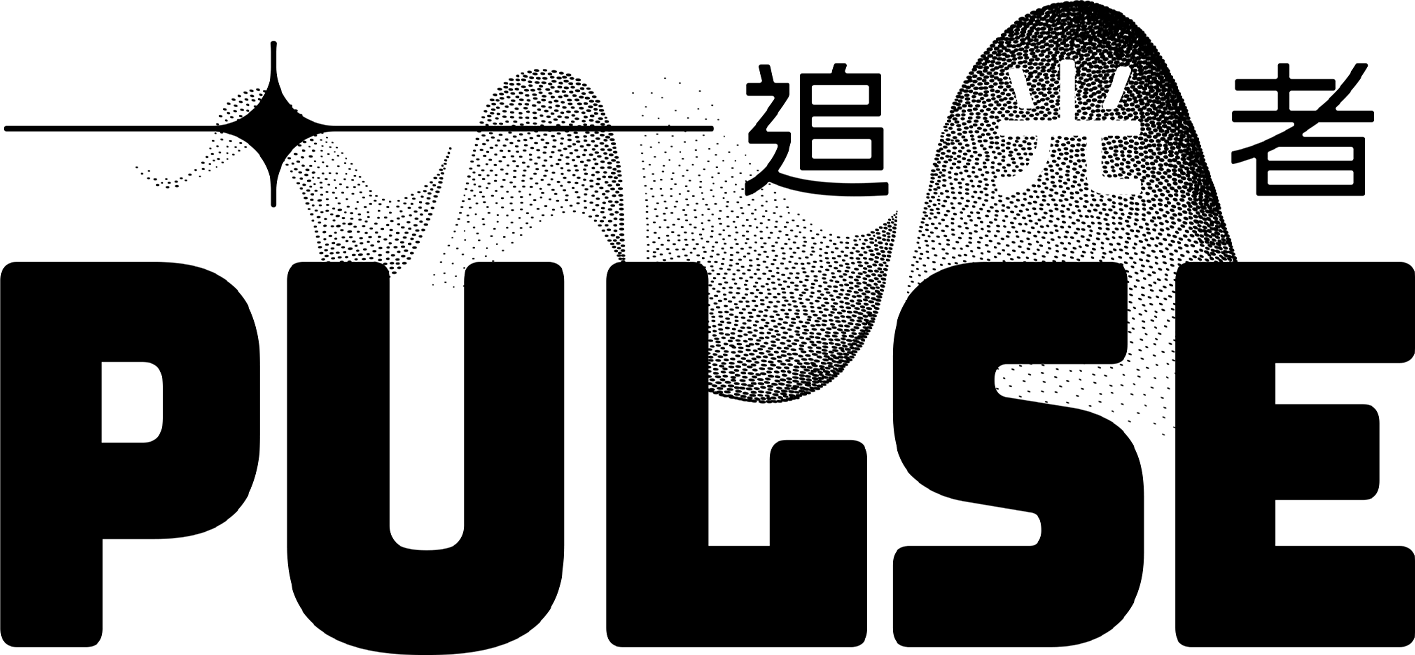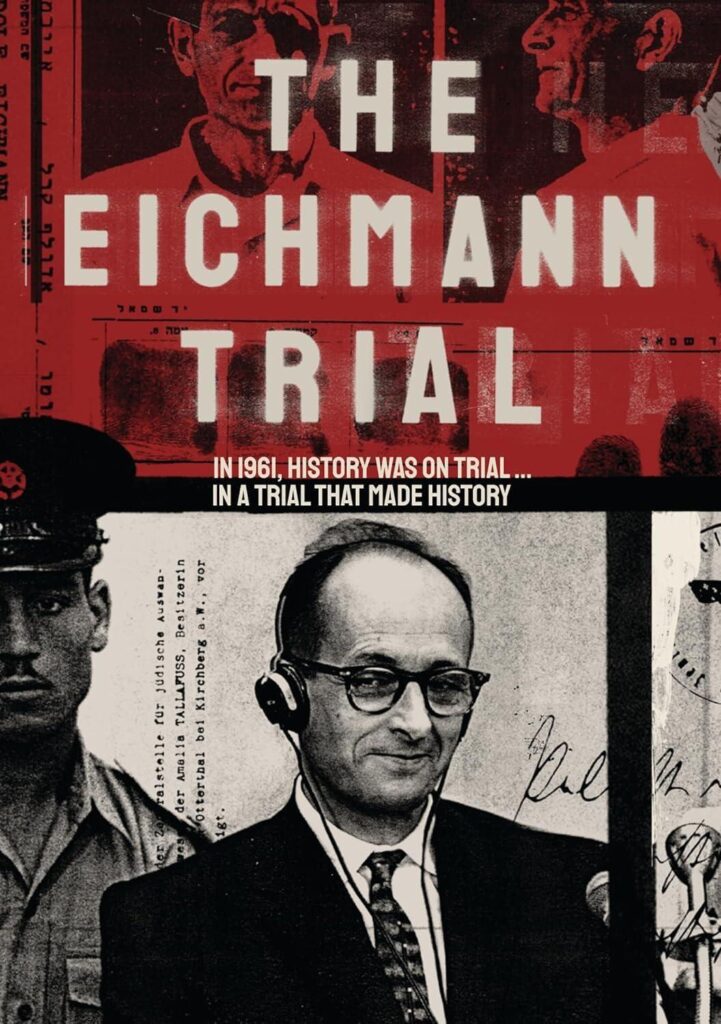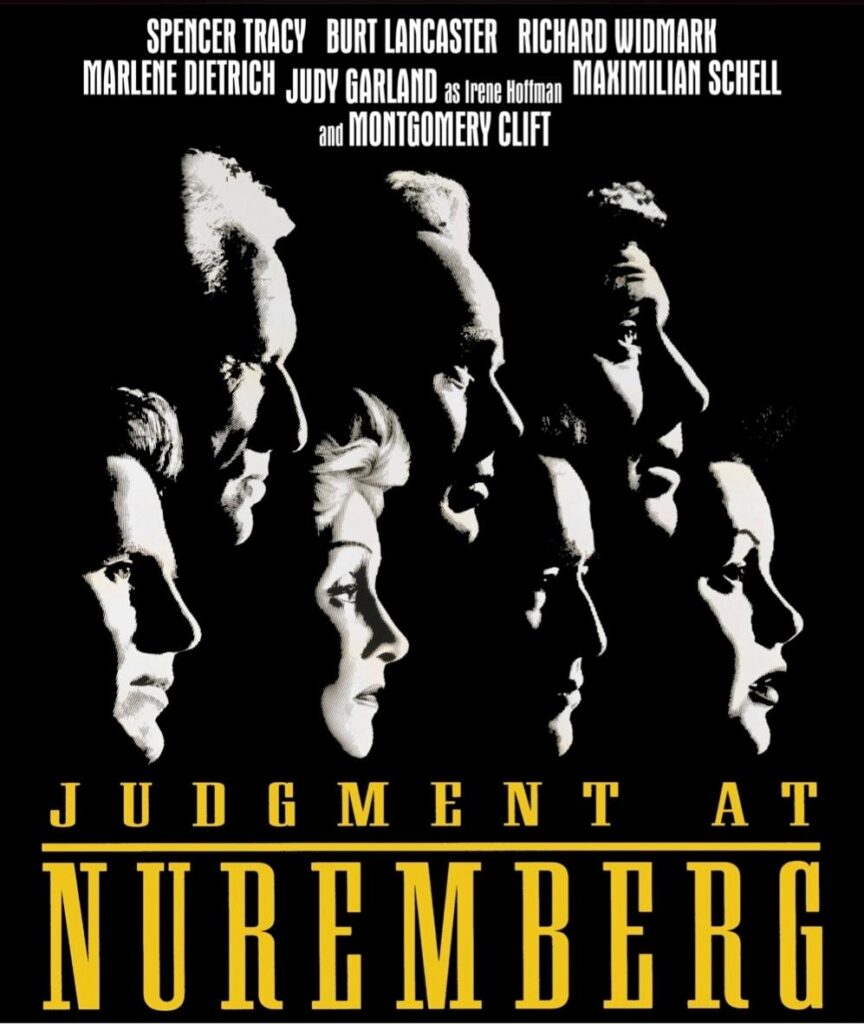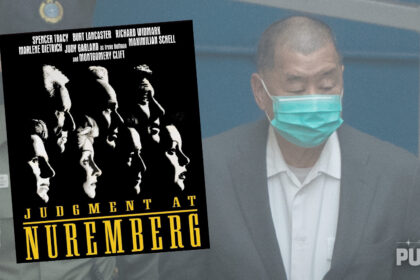引言:邪惡的多重面向
當我們試圖理解二十世紀最黑暗的歷史篇章時,「邪惡」這個概念往往顯得過於單薄,無法承載納粹暴行所呈現的複雜人性圖景。鄂蘭(Hannah Arendt)在耶路撒冷審判艾希曼(Adolf Eichmann)時提出的「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概念,徹底顛覆了傳統對邪惡的理解——邪惡不必然來自惡魔般的意志,而可能源於思考能力的徹底缺失。然而,艾希曼所代表的僅是邪惡光譜中的一端。戈林(Hermann Göring)作為納粹政權的二號人物,展現了另一種截然不同的邪惡形態:他聰明絕頂、深諳權謀,完全清楚自己在做甚麼,卻依然選擇走向深淵。而1961年克雷默(Stanley Kramer)執導的電影《紐倫堡大審判》(Judgement at Nuremberg 1961)則揭示了第三種更為幽微的邪惡:法學教授出身的揚寧法官(Ernst Janning),一個曾經備受尊敬的法律權威,如何在納粹體制下成為司法謀殺的共謀者。
這三種邪惡的類型學為我們提供了反思人性與道德責任的豐富素材。艾希曼代表了官僚體系中「無思」的執行者,戈林體現了權力慾望與意識形態狂熱的結合,而揚寧則展示了知識分子在極權體制下的道德困境與最終墮落。三者共同構成了一幅關於邪惡如何在不同人格類型中生根發芽的完整圖景。
1. 艾希曼與平庸之惡——無思的深淵
1961年,鄂蘭以《紐約客》特派記者的身份前往耶路撒冷,報導對艾希曼的審判。作為一位曾經逃離納粹迫害的猶太裔哲學家,鄂蘭原本預期會看到一個惡魔般的人物——一個與他所犯下的滔天大罪相稱的怪物。然而,她在法庭上看到的卻是一個令人困惑的平庸之人。艾希曼既不瘋狂,也不充滿仇恨;他不是一個狂熱的反猶主義者,甚至不是一個特別有主見的人。他只是一個普通的官僚,一個熱衷於按時完成工作、追求職業晉升的小人物。
鄂蘭在她的報導中寫道,艾希曼最令人不安之處在於他的「正常」。心理學家對他進行了詳細的評估,結論是他在精神上完全正常,甚至在某些方面「令人欽佩」— 他是一個盡職的丈夫和父親,一個可靠的同事。正是這種正常性構成了「平庸之惡」的核心悖論:最可怕的罪行可以由最普通的人犯下,而這些人既不需要特殊的邪惡動機,也不需要異常的人格特質。
鄂蘭對艾希曼的分析最終凝結為一個核心概念:「無思」(thoughtlessness)。這裏的「思」不是指智力或計算能力 —艾希曼在組織運輸、協調後勤方面展現了相當的行政才能 — 而是指反思性的思考,即審視自己行為的道德意涵、從他人角度思考問題的能力。艾希曼缺乏的正是這種思考能力。他從未真正思考過自己在做甚麼,未想像過那些被他送往集中營的人的處境,也未質疑過他所執行的命令的正當性。
這種無思不是天生的缺陷,而是一種主動的放棄。艾希曼選擇不去思考,因為思考會讓他的工作變得困難,令他無法安心地完成上級交付的任務。他用陳腔濫調和官方語言包裹自己,用「我只是在執行命令」這樣的藉口來逃避道德責任。在鄂蘭看來,這種對思考的放棄本身就是一種道德上的失敗,甚至可以說是一種罪行。
艾希曼案例中另一個令人矚目的特徵是語言的作用。艾希曼在法庭上的陳述充斥着官僚術語和納粹宣傳的套話。他談論「最終解決」時仿佛在討論一個純粹的行政問題,用「轉運」和「疏散」來描述對數百萬人的謀殺。這種語言的扭曲不僅是一種掩飾,更是一種自我欺騙的機制。透過使用這些去人性化的術語,艾希曼得以將自己與暴行的道德意涵隔離開來。
鄂蘭敏銳地觀察到,極權主義對語言的操控是其最有效的統治工具之一。當屠殺被稱為「特殊處理」,種族滅絕被包裝為「最終解決」,受害者被降格為數字和統計資料時,道德感知就已經被系統性地腐蝕了。艾希曼不需要克服任何道德障礙來執行他的工作,因為他所使用的語言已經預先消除了這些障礙。
鄂蘭的「平庸之惡」概念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爭議,許多人認為這是在為納粹罪犯開脫,或是在淡化大屠殺的恐怖。然而,鄂蘭的意圖恰恰相反。她試圖揭示的是一個更加令人不安的真相:邪惡並非某些特殊個體的專利,而是潛伏在每一個放棄思考的普通人身上。艾希曼的可怕之處不在於他是一個怪物,而在於他太過正常,有太多人可能成為他。
2. 戈林與權力之惡——清醒的墮落
如果說艾希曼代表了邪惡的平庸面向,那麼戈林則展現了邪惡的另一種可能性:一種完全清醒、充分知情的惡。戈林是納粹黨的元老成員,希特勒最親密的戰友之一,帝國的第二號人物。他創建了蓋世太保,主持了四年經濟計劃,指揮了德國空軍,並在納粹體制中積累了巨大的權力和財富。與艾希曼不同,戈林絕非一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他是決策核心圈的成員,完全了解納粹政權的本質和目標。
最新的紀錄片和歷史研究更加清晰地呈現了戈林的複雜性。他聰明、有魅力、能言善辯,在紐倫堡審判中展現出驚人的辯才,多次讓檢察官陷入困境。他不是一個狂熱的意識形態信徒,而更像是一個機會主義者,一個被權力和奢華生活所吸引的人。然而,正是這種清醒使他的罪行更加不可原諒。
戈林與艾希曼的根本區別在於意識的清晰程度。艾希曼可以聲稱他只是在執行命令,他不知道全貌,他只是一個小齒輪。但戈林不能做出同樣的辯護。他坐在權力的頂端,參與了最重要的決策,完全清楚納粹政權在做甚麼。他簽署了開啟「最終解決」的文件,主持了掠奪猶太人財產的會議,批准了在佔領區實施的殘酷政策。
這種明知故犯使戈林的邪惡呈現出一種不同的質地。如果說艾希曼的罪在於他的無思,那麼戈林的罪在於他的有思卻不為所動。他思考,知道,也理解 — 然後他選擇繼續。這種選擇不能歸咎於無知或愚蠢,而只能歸因於道德感的徹底敗壞,或者說,對權力的追求壓倒了一切其他考慮。
戈林的案例揭示了權力對人性的腐蝕作用。年輕時的戈林是一位戰爭英雄,一個受人尊敬的飛行員。但權力的滋味一旦嚐到,就很難放下。為了維持和擴大自己的權力,戈林願意做任何事情:包括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暴行的共謀者。
這種權力慾望如何導致道德麻痺?一個可能的解釋是,當一個人完全沉浸在權力的遊戲中時,其他人就不再是道德考量的對象,而只是實現目標的工具或障礙。受害者的苦難變得抽象而遙遠,而權力的得失則是真實而緊迫的。戈林可能從未停下來真正想像那些因他的決定而死去的人的面孔和故事,因為那樣做會干擾他的政治算計。
紐倫堡審判為我們提供了觀察戈林人格的獨特窗口。在法庭上,戈林表現得自信滿滿,甚至帶有某種傲慢。他試圖為納粹政權辯護,將自己塑造成一個愛國者而非戰犯。他的辯護策略是承認德國發動了戰爭,但拒絕承認戰爭罪和反人類罪,試圖將一切歸咎於「戰爭的必要性」。
最終,戈林被判處絞刑,但他選擇在行刑前服毒自殺。這個最後的選擇本身就說明了很多。一方面,它顯示了戈林對控制的執着——即使在死亡面前,他也要掌握主動權。另一方面,它也暴露了他的道德破產——他至死都不願面對自己罪行的後果,不願以一個被定罪的戰犯的身份走向絞刑架。
戈林所代表的邪惡類型對傳統的道德哲學構成了嚴峻的挑戰。在柏拉圖以來的西方哲學傳統中,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沒有人會故意作惡,因為作惡必然損害行為者自身。根據這種觀點,所有的惡行都源於某種形式的無知或錯誤。然而,戈林的案例似乎反駁了這一觀點。他知道自己在做甚麼,知道這些行為按照普遍的道德標準是錯誤的,但他仍然選擇這樣做。
這是否意味着存在某種純粹的惡意,一種不能還原為無知或錯誤的邪惡意志?還是說,戈林的選擇最終仍然可以用某種形式的自我欺騙或道德視野的狹隘來解釋?這些問題沒有簡單的答案,但它們迫使我們面對人性中最黑暗的可能性。
3. 揚寧法官與體制之惡——知識分子的墮落
1961克雷默執導的電影《紐倫堡大審判》選擇了一個獨特的視角來審視納粹罪行:不是控訴那些直接執行屠殺的人,而是審判那些使屠殺成為「合法」的法官們。電影的虛構核心人物是揚寧 ,一位曾經備受尊敬的法學教授和法官,在納粹上台之前就已經建立了崇高聲譽的法律權威。
揚寧的案例提出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問題:一個致力於法律和正義的人,如何能夠成為司法謀殺的工具?知識分子在極權體制下應當承擔甚麼樣的道德責任?當法律本身被扭曲為壓迫的工具時,服從法律還是一種美德嗎?
揚寧法官所代表的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共謀者:專業人士。他不是一個無知的執行者,也不是一個權力狂熱的政客,而是一個受過最好教育、擁有最高專業素養的法律人。正是這種專業身份使他的墮落更加令人震驚,也更加具有警示意義。
電影中,揚寧承認他知道納粹的種族法律是不公正的,他知道那些被他判處死刑或絕育的人是無辜的。但他仍然做出了那些判決,因為他相信維護法律體系的權威比任何個案的正義更重要,因為他認為德國需要秩序和穩定,因為他害怕如果不合作會發生甚麼。這些理由聽起來似乎有些道理,但它們最終都無法為他的行為開脫。
揚寧的案例折射出一個更廣泛的問題:納粹統治下德國知識分子的集體沉默和共謀。大學教授們繼續教書,法官們繼續判案,醫生們繼續執業 — 彷彿一切正常。這種表面的正常恰恰是極權主義得以運作的條件。當社會的精英階層願意與政權合作時,抵抗就變得幾乎不可能。
這種共謀不一定是出於認同或熱情。許多知識分子可能私下對納粹的暴行感到不滿,但他們選擇了沉默和服從。這種選擇有各種各樣的理由:對家人的擔憂、對職業的考量、對自身安全的恐懼、對改變現狀的無力感。但無論理由如何,結果都是一樣的:他們的沉默成為了暴行的許可證。
揚寧的辯護律師在電影中提出了一個有力的論點:如果要審判揚寧,就應該審判整個德國社會,包括那些與納粹合作的外國政客和商人。這個論點指向了一個真實的困境:在一個腐敗的體制中,幾乎沒有人能夠完全免於牽連。
然而,電影最終拒絕接受這種「人人有罪故無人有罪」的邏輯。審判長海伍德法官在判決中明確指出,即使在極端情況下,個人仍然保留着道德選擇的能力和責任。揚寧本可以辭職,可以拒絕執行不公正的判決,也可以用他的專業知識和社會地位來抵抗暴政。他選擇不這樣做,這個選擇本身就是他的罪行。
電影的高潮之一是揚寧決定打破沉默,承認自己的罪行。這個決定來自於他與另一位被告的對比 — 那位被告至死都在為納粹辯護,堅持認為他們做的一切都是對的。揚寧不願意被歸入這一類。他知道他們做的是錯的,知道那些判決是不公正的,現在願意承認這一點。
揚寧的承認並沒有減輕他的罪責,但它恢復了某種道德清醒。透過承認,他重新確認了對錯的區分,承認了自己的道德主體性。這與艾希曼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艾希曼至死都不承認自己做錯了甚麼,因為他從未真正理解過道德的含義。
揚寧的案例對當代知識分子具有特殊的警示意義。作為社會的思想者和教育者,知識分子享有特殊的地位和影響力,因此也承擔着特殊的責任。當一個社會走向邪惡時,知識分子有責任發出警告,有責任抵抗,至少有責任拒絕合作。沉默本身就是一種選擇,而在某些情況下,沉默就是共謀。
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輕易站在道德高地上譴責那些在極權體制下做出妥協的人。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抵抗是有代價的,有時是生命的代價。但這恰恰是為甚麼我們需要在極端情況到來之前,就培養道德勇氣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揚寧的悲劇不僅在於他最終的選擇,也在於他之前的整個人生沒有為他在關鍵時刻做出正確選擇做好準備。
(待續)
張燦輝
流亡哲學人
2026年1月18日
台灣新北市林口晴空樹
《橫流集》專欄系列之前其他文章,請到《追新聞》網站瀏覽:https://thechasernews.co.uk/t/橫流集/
相關新聞
- 2026 年 01 月 01
- 2026 年 01 月 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