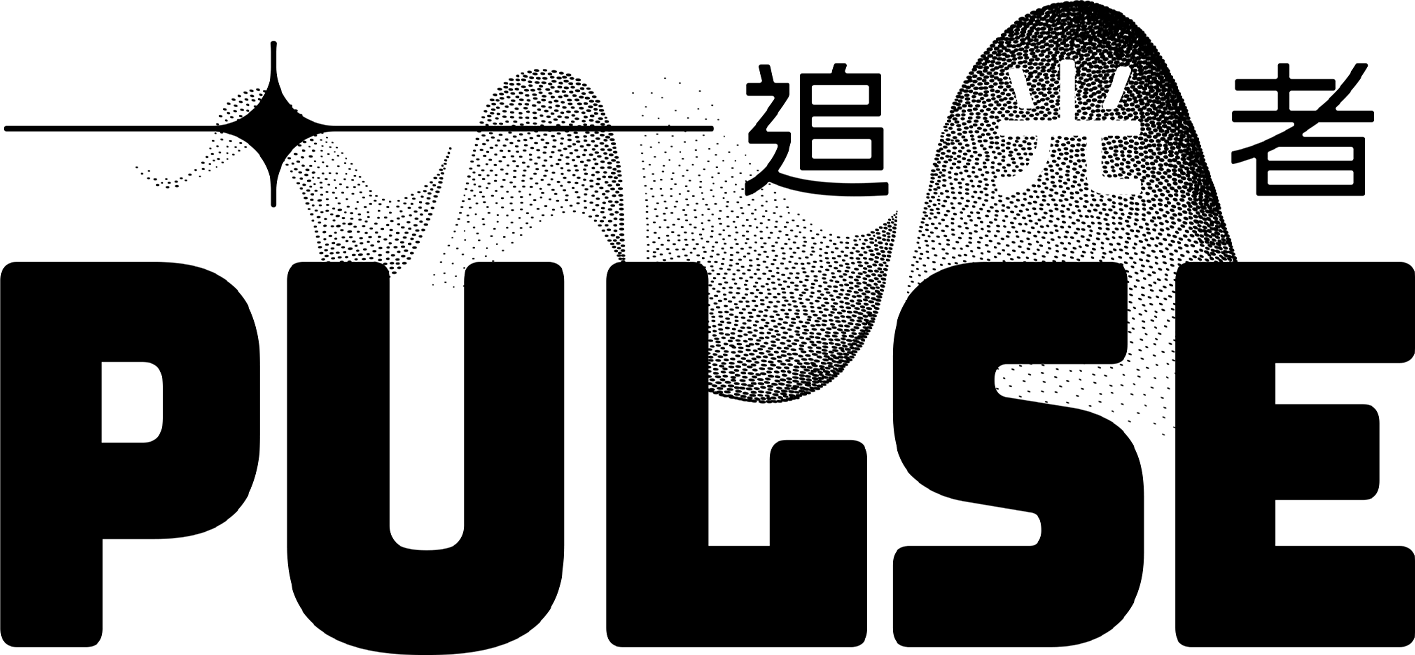作為維護法治的最高首長,張舉能主動擴大《國安法》的適用範圍,被動地背棄捍衞人權的責任。
在2020年《國安法》通過前,香港終審法院往往會負起捍衞人權和自由的重要責任,這可以從他們的判詞看出,例如:
- 1999年吳嘉玲案:終審法院强調:「(權利)必須獲得寬宏的解讀才能最大限度地提供根本的保障」((Rights) must receive a “generous interpretation” to secure the “full measure” of fundamental protections ,見 Ng Ka Ling v HKSAR [1999] 2 HKCFAR 4 at para 77)。
- 1999年吴恭劭案:終審法院強調「對表達自由的限制必須盡量狭窄」(restrictions on expression must be “narrowly interpreted”)(HKSAR v Ng Kung Siu [1999] 2 HKCFAR 442 at para 46)。
- 2005年梁國雄案,終審法院强調法庭在涉及保護基本人權時,法庭必須「在保護基本權利時時刻保持警惕,有力地審視任何限制,並對太過嚴苛的做法宣布其為不合憲」(remain “vigilant” in protecting fundamental rights, rigorously scrutinizing any restriction, and declaring overreaching provisions unconstitutional while prescribing remedies or excisions where necessary and appropriate, 見 Leung Kwok Hung v HKSAR [2005] 3 HKLRD 164 at paras 16 and 77-79 )。在該案中,終審法院强調「終審法院有一個主動要負的責任就是對所有涉及憲法的上訴案保持高度警惕。(the CFA bears a proactive duty to remain vigilant on all constitutional issues related to an appeal—even if they do not directly arise on appeal (para 78))。終審法院說:「毋庸贅言,一個法治的社會,法庭在保護基本人權中必須保持高度警戒,並嚴格審視任何對人權施加限制的措施」(Needless to say, in a society governed by the rule of law, the courts must be vigilant in the protection of fundamental rights and must rigorously examine any restriction that may be placed on them. (FACC Nos. 1 & 2 of 2005, para 16))。
這些判詞說明,在《國安法》頒布前,香港的絡審法院對事關保障人權和思想言論自由的事件是有過積極嚴厲的違憲審查的先例的。很可惜這些充分維護人權和自由的判詞,在《國安法》通過後變成不值一文的廢紙。從張舉能在上述黎智英案(2021)、伍巧怡案(2021)及譚得志案(2024)可以看出,過去終審法院充滿捍衞人權與自由的判詞完全失效。
張舉能除了不顧香港終審法院以前捍衞自由和人權的判决,更無視國際社會確立的捍衞言論自由與人權的共識。在「羊村繪本案」和「譚得志案」中,辯方均提出國際普通法社會認可的「錫拉庫扎原則」(Siracusa Principles)作為抗辯理由,可惜法官輕蔑地表示這個公約已經過時而不適用於香港,但卻没有提供足够的論據。「錫拉庫扎原則」是1984年由31名國際法專家,在意大利舉行的一個學術會議上經討論後同意的原則,旨在就《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中有關限制人權的條文如何解讀,提供詳細指引。法律評論員黃啟暘在接受《法庭線》訪問時指出:「根據《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此等反映當代公法學者共識的權威著作,本來就是確定國際法原則的補助資料。終審法院事實上曾不只一次引用『錫拉庫扎原則』,解釋《香港人權法案條例》,尤其是何謂『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衞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的重要依據。雖然,『錫拉庫扎原則』等人權標準,嚴格來說並不約束香港,但法庭考慮人權案例時,並非要求其與香港情況一模一樣才能適用,而是案例背後的價值,以及如何限制政府權力。很多國外案例訂均遵從其基本原則,即:除非內容涉及煽動暴力,否則不應該將煽動刑事化。然而,郭偉健在判詞中,僅表示香港情況特別、2019年曾發生動亂,就視『錫拉庫扎原則』過時及不適用,就輕蔑地否定該原則的適用性。」(見《法庭線》「羊村繪本案判詞解讀」2022/10/30 [4])。對郭偉健這個判決,張舉能沒有作出任何糾正。
張舉能不但忽視香港終審法院以前的判例和國際司法界的共識,反而主動擴大《國安法》的適用範圍。
在「羊村繪本案」(HKSAR v. NG Hau Yi Sidney (伍巧怡) [2021] HKCFA 42)中,控方引用國安法嚴厲的保釋條件而不准被告保釋,被告上訴,理由是「煽動罪」並不是《國安法》的罪名,不應該適用《國安法》嚴厲的保釋條件。雖然《基本法》23條有此罪名,但案發時23條尚未立法。《基本法23條》的立法,要等到2024年3月8日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Safeguarding National Security Ordinance,簡稱 SNSO),正式把「煽動罪」納入國家安全罪後(即原來的 CO 9-10 納入SNSO 24)才能够適用國安法下較嚴苛的司法程序。
所以辯方挑戰適用《國安法》嚴苛的保釋條件有違憲之嫌。但終審法院卻裁定上訴人敗訴,它的理由是:「《基本法》23條和《國安法》第7條合併起來就清楚地說明煽動罪符合危害國家安全的罪名」(The combined effect of BL 23 and [HKNSL 7] is therefore to make it clear that a prohibited act of sedition – including an offence contrary to section 10(1)(c) of the Crimes Ordinance – qualifies as an offence endangering national security)(para 7)。認為兩條法例「並肩而行的」(in tandem)(見 Ng Hau Yi Sidney [2021] at paras 5 20–21, 24, 27).
同樣,在「譚得志上訴案」中,終審法院雖然承認,在案發時《基本法23條》尚未立法,只能够以 《刑事犯罪條例》第9及10來起訴他們 “Such a sedition offence [under CO s 10(1)(b)] was not covered by the NSL and it continued to exist as an offence under the CO… until the pertinent provisions were repealed by the… SNSO… on 23 March,2024”。卻認為《刑事犯罪條例》可以與《國安法》 並肩而行,從而適用《國安法》嚴苛的保釋條件。
終審法院這樣做,對「法治」造成很嚴重的衝擊:
- 它大大擴張了《國安法》的適用範圍。它把該法建立的嚴苛的司法程序、量刑標準、假釋條件擴展到非該法所針對的四項罪行(分裂國家、顛覆中央政權、勾結外國勢力、恐怖主義)而適用到其他罪行。
- 擴大《國安法》的適用范圍,影響了香港原有的刑事司法程序。例如在「伍巧怡案」中,採用了《國安法》的嚴格保釋條件,被告不獲保釋,成為變相「有罪推定」。在「譚得志案」中,法庭裁定即使被告按《刑事罪行條例CO9及10》被起訴煽動罪,《國安法》內免除陪審團參與審訊的安排,依然適用。這就實際上剝奪被告獲公平審訊的機會。
- 擴大《國安法》的適用範圍,使得本港原有的量刑制度都趨於嚴厲。例如在「呂世瑜案」中,本來被告在認罪後可獲扣减刑期的對待,但判詞卻說:《國安法》第21條就情節嚴重案件,訂明「處五年以上 …有期徒刑」的罰則,屬強制性規定。本地量刑法律及原則,應在《國安法》條文訂下的量刑框架內運作。這樣,被告就無法獲得减刑的對待。(按:香港刑罰有訂最高刑期,卻沒有訂最低刑期,現在的做法就是把大陸最低刑期的做法引入香港)。
- 擴大《國安法》的適用範圍,改變了「法律不究既往」的重要普通法原則。例如在「張敬生案」中(港大評議會時任主席張敬生的人身保護令的申請),張敬生被判的是《侵犯人身罪條例》下的煽惑他人有意圖傷人罪,但這卻被視為涉及國家安全的罪行。當日張敬生承認這控罪,控方則同意撤銷《國安法》的控罪,但在服刑近一年後,《監獄規例》才作出修改,並具追溯效力,改變他因行為良好而獲假釋的機制。這就開創了法例具有追溯力的惡果。
這都是終審法院通過擴大《國安法》的適用範圍,改變了香港的刑法制度的例子,這些做法客觀上是等同引入了大陸的刑法制度。
程翔
2026年1月
[4] https://thewitnesshk.com/羊村繪本案判詞解讀%E3%80%80法官判詞釐清了甚麼界線?/
相關新聞
- 2026 年 01 月 29
- 2026 年 01 月 30
- 2026 年 01 月 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