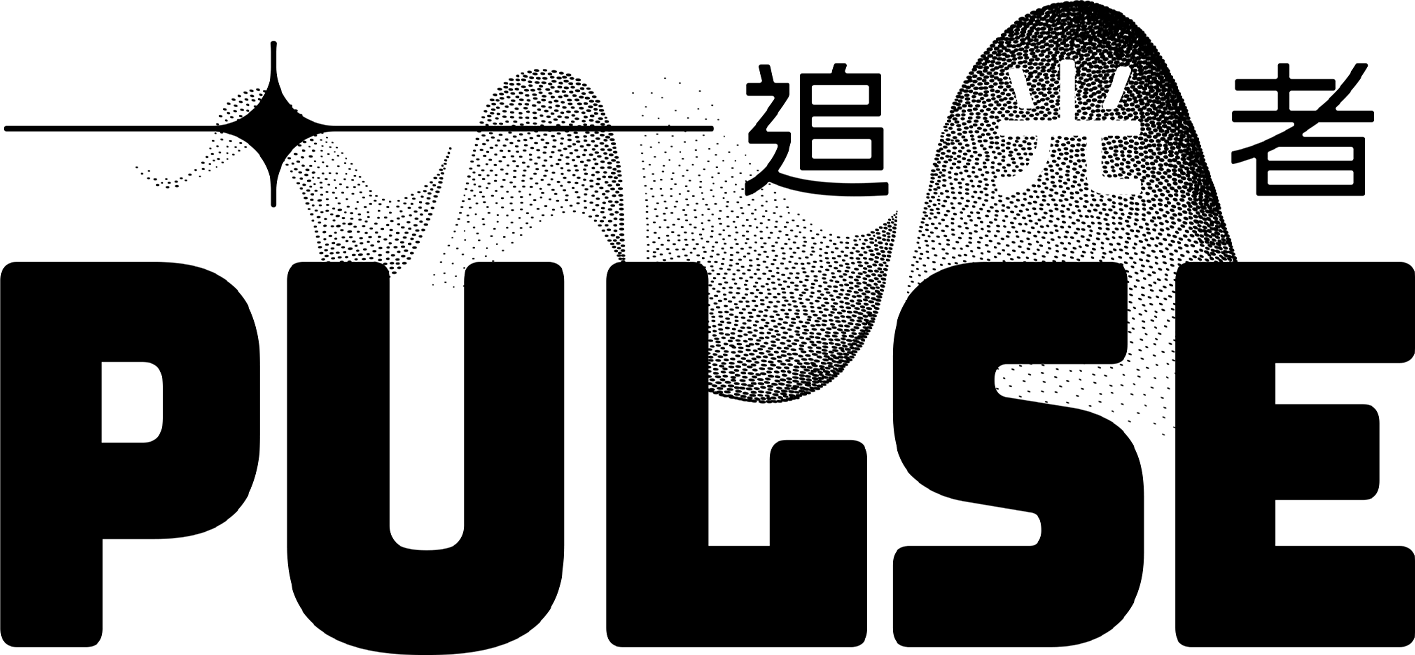一、在滄海橫流中回望前輩
二○一九年之後,我的人生發生了根本性的斷裂。
我離開生活、教書超過七十年的香港,成為一名流亡者。這不是旅居,也不是退休後的閒適移居,而是在威權統治下的出走。在《香港已死?》裏,我說:這是「取無家的自由,而不願意在白色恐怖下過奴役的生活」的選擇,代價是「家」的瓦解、親人和朋友的遠離與城市的死亡感。
流亡讓我重新回望前輩。當我在台灣林口的書房裏重讀唐君毅、牟宗三,既像在對話,也像在清算。原來,我所走的路,早在上一個世紀已有人走過、有人跌倒、有人留下腳印。我這一代香港哲學人,不過是接續了中國思想史上第三代、第四代的流亡者,只是這次流亡的名義,不再只是「中國」的飄零,更是「香港已死」的哀歌。
作為一個現象學者,我無法只把流亡當成歷史背景或政治標籤,而必須把它當作一種存在狀態來細察:一個被迫離開熟悉世界的「此在」,如何在斷裂中安頓自己?「家」還有沒有可能?「哲學」還能否在廢墟上繼續?這些問題,使我必須回到上世紀那些「南來避秦」的哲學人身上 — 尤其是牟宗三和唐君毅 — 看他們如何在無家可歸的時代,維持對哲學和道德的信念。
二、牟宗三:我在新亞書院課室裏的老師
我和牟宗三先生的相遇,並不是透過書本。那時我還是中大哲學系的學生,上過先生課,也有幸和先生在九龍農圃道新亞書院圓亭下過圍棋 (當然是他讓我四子)。對當年的我來說,他首先是「老師」,是站在黑板前寫字、在講台上闡釋「心性」、「良知」、「康德知識論」的學者,而不是「流亡者」。我聽不懂他的山東口音的國語,是以也不太明白他的哲學論述,只知道他是哲學大師。
那個年代,我們關心的是課程內容、哲學立場與考試成績。牟先生在課上談康德的先驗綜合判斷、談道德形上學如何可能,也談儒家心性論如何與現代哲學對話,但在我們耳裏,這些詞彙更多像是哲學概念,而不是他個人生命的傷口。
直到多年以後,我在牟先生的〈存在主義入門〉讀到那段極為私人、幾乎是自白式的文字,才真正被震撼。他說自己「由七七事變時起開始流亡,一直流亡到現在,流亡到這裏」,整整三十年「一直都是在流亡,在逃難,而且不單是轉換空間那麼簡單,而是在動亂中,在恐怖中」,以致「內心裏總是沒有安全感的」。
在這樣的生命背景下,他引入存在主義那句名言:「人是最不安全無保證的一個存在」;又談到「人是無家的,這就是存在主義所說的人的無家性(homelessness)」,並引耶穌的話為喻:「飛鳥有巢,狐狸有洞,人之子無家可歸。」 但他緊接着指出,存在主義說人的無家性,「並不是單當作一個概念去了解,而是要我們在『存在的遭遇』中去作『存在的感受』」,而他自己與那一代中國人在戰亂、政權崩解、長期流亡中,「現在卻真有了這存在的遭遇,而我個人也的確有這存在的感受」。
這裏,牟宗三不再是純粹的「康德—儒家形上學家」,而是一個流亡者在為自己發聲。他說:「存在主義是教我們在這存在的感受中正視這人的無家性,不得逃避,不得掩耳盜鈴,不得自欺,過那虛偽(不真實)的人生。」這段話對我這個後來也成為流亡者的人來說,幾乎像是一個跨越幾十年的囑咐 — 他要求自己那一代人,不可以用「大義」或「歷史使命」來遮掩內心的不安與無根,而要正視那種「內心總是沒有安全感」的存在狀態。
更震耳的一句,是他談到一位來台灣旅遊、喜歡談存在主義的美國人時說:「他們來台灣只是享樂,而我們在台灣卻是逃亡。此實不可同日而語。」在他眼中,沒有經歷過真正「生死交關」的歷史震盪與流亡經驗的人,很難真正理解存在主義所說的「無家性」。這裏,他把存在主義從一種「理論流派」轉化成一種「存在感受」:只有在歷史暴力前真正跌宕過、在恐怖中長期沒有安全感的人,才能切實體會存在主義的深意。
他進一步做出激烈的判斷:「流亡絕不是邏輯的事,亦不是理論或觀解的事。流亡不是一些『理』,而是切切實實的生死交關。」他批評自希臘以來西方傳統哲學「其本質都是邏輯的、理智的、或觀解(theoretical)」,因此是「非存在的」(non-existential),不能正視人的歷史性、偶然性、不安性、無家性,只憑空抽象地講人的本質;連宗教亦淪為「虛偽的、庸俗的」。存在主義的貢獻,在於直指傳統哲學是 non-existential,為「二十世紀不安時代」帶來一個大轉捩。
這一整段,其實就是牟宗三對「流亡哲學人」角色的自我定位:一方面,他深知流亡不是理論可以包辦的,而是「切切實實的生死交關」;另一方面,他又不願止於頹喪與墮落,強調存在主義要求我們「正視這無家性,要在無家中找尋你的家,不得安於這家性中而成為鬼混,成為頹廢」。如若只是在無家狀態中「鬼混與頹廢」,那只不過是「墮性的家」,是「虛偽的人生,而不是存在主義」。
後來我在流亡歲月中反覆咀嚼這些話,愈來愈感到:牟宗三的存在主義論,其實就是他的「流亡自白」。他把無家性、恐怖、不安與長期流亡的經驗內化為存在主義的感受,再用儒家與康德的語言去超越那種墮落的無家,尋找一種「在無家中仍不鬼混」的道德站立方式。
對我這個曾在他課室裏做學生的人來說,最深的震撼是:當年站在講台上侃侃而談哲學體系的老師,其實是那樣一個在戰火、逃難與政治恐怖中被拋擲了三十年的人。他在文字裏寫下的那句「三十年來一直都是在流亡,在逃難」,如今也可以用來形容我這一代香港人的命運,只是我們流亡的名義和地理路線不同。牟宗三給我的,不只是儒家與康德的理論,更是一種在無家、無保證、無安全感中仍堅持不自欺的存在範式。
三、唐君毅、徐復觀、錢穆:花果飄零與靈根自植
在我的流亡思考中,唐君毅始終佔據一個矛盾的位置:我既深受他的感召,又不斷與他爭辯。當年在中大修讀哲學時,我拜讀他的「花果飄零及靈根自植」,那時只覺得語言深邃而高遠,並未真正意識到那是他自己一生流亡經驗的凝縮。他說,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如同一棵被連根拔起的大樹,樹幹崩倒,花果飄零,到處流散;但只要我們懂得在每一處落腳之地「靈根自植」,那麼即使身在他鄉,仍然可以活出真正的中國人之靈。
這種隱喻對我很有吸引力。多年後流亡英國,我寫下「在家流亡」與「我們還有家嗎?」這些文章時,仍習慣用「靈根」來思考:當地理的家園被毀、法律上的家園被佔據,我們還能否在人與人的關係、在語言與記憶中找到某種精神上的家?
然而,唐君毅的說法也有時讓我感到不安。他所說的「中國人」有一種強烈的本質感,彷彿只要堅守儒家的心性之學,不論在香港、台灣、北美,都可以安然自處。可是對於香港這個本身就被殖民、再殖民的城市而言,「中國」從來不是單純的精神母體,而是一個充滿暴力與矛盾的命題。在雨傘運動與反修例運動之後,「中國」對許多年輕香港人而言,尤其是對我,更像是壓迫的來源而不是安頓的所在。
徐復觀和錢穆,則以另一種方式書寫流亡。徐復觀在回顧 1949 後的歲月時說,這一代「在九死一生中流亡海外」的知識分子,正好應該趁機做「政治上大反省」與「文化思想上大反省」— 他在香港創辦《民主評論》,就是在流亡處境中思考中國為何會落入極權統治,並試圖為中國自由主義與儒家價值哲學尋找新出路。
錢穆則自認為「流亡知識分子」,但他更願意把自己講成「一生為故國招魂」的史家。他在香港創立新亞書院,在台灣寫《國史大綱》,在美國講學,彷彿一生都在為那個已失去的「中國」守靈。
這些前輩教會我的,是一種深沉的責任感:流亡不是遁世,而是被迫離開獨裁專制後,仍然不願放棄對公共事務的思考與介入。只是,他們的流亡敘事幾乎總是以「中國」為單位,而我這一代,卻不得不問:當「香港」成為我們真正的故鄉,而「中國」在政治與情感上日益陌生時,我們還能否直接繼承「靈根自植」的語言?
四、遲來的理解:我與老師們的流亡
我在中文大學修讀哲學的年代,唐君毅、牟宗三還在山城,那時的我,只把他們當成課室裏的「哲學大師」,而不是流亡者。多年以後回想起來,才發現這一點,是我一生中最深的遺憾之一。
那時在課堂上,他們談的是「心性」、「內聖外王」、「中國文化的前途」,語氣往往平靜而莊重,很少用第一人稱說「我在流亡」、「我失去家園」。我們年輕,專注在文本、理論與考試,聽到「花果飄零」、「靈根自植」,也更多當作抽象的哲學隱喻,而不是坐在台上的那位老人親身經歷過的流離失所。
後來,我成為勞思光的親近學生,與他相處的時間更多。即使如此,我仍然很少真正追問他們的「流亡」感受:他們怎樣走出大陸?在香港初來乍到時住在哪裏?那時對未來是絕望還是僥倖?他們如何看待「香港」這個暫時的棲身之所?這些問題,我幾乎沒有在年輕時認真問過。
幾十年過去,我自己也成為流亡者,才忽然意識到:當年坐在講台上的,不只是哲學老師,而是失國、失家、失去整個語境之後,仍然在課室裏談「道德」、「自由」、「人性尊嚴」的哲人。他們身體裏背負的,是一整代人的破碎與哀痛,而我卻只忙着做一個認真、甚至有點「功利」的哲學系學生,關心學術論文寫得如何,本科畢業後何處讀研究院,能否申請獎學金等等,卻沒有細聽那背後的生命顫動。
這種遲來的體悟,帶着一種深刻的遺憾感:我錯過了直接向他們請教流亡傷口的機會,沒有聽他們談午夜失眠、離散親人、對大陸與香港複雜感情的那些時刻。等到我自己被迫離開香港,才真正懂得「無家」是怎樣的空虛,如何的孤獨,那些一生足以拖不完的鄉愁與責任感,原來他們早就經歷過,只是我們當年不懂。
也正因為這個遺憾,近年我才特別執着於把「流亡」寫出來、說出來:在《思.香港》三部曲和《香港已死?》中,我一再嘗試用哲學語言、也用情感語言,去描繪流亡者的無家、憤怒與堅持。某個意義上,這既是在為自己這一代香港人的流亡立案,也是在補寫當年我沒有好好聽懂的老師們:把我今天的感受,回過頭投射到他們的生命史裏,讓讀者在我的書中,多少聽到一些當年我沒有抓住的聲音。
如果說這段遺憾有甚麼正面意義,大概就是:它逼我承認,哲學不只是概念與體系,更是具體生命在歷史裂縫中的掙扎。當我們重讀唐君毅的「花果飄零」、牟宗三對「虛偽時代」的嘆息、勞思光對中國哲學命運的焦慮時,不應只把它們當成學理,而要記得,那是流亡者在異鄉小書房裏、在租住的狹窄房間裏,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自白。
我沒有在他們還在世的時候好好追問,已經無法挽回。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的流亡歲月裏,讓這份遲來的理解轉化為文字與教學,提醒後來的學生:當你坐在課室裏聽一位「哲學人」說話時,別只看見他講義上的概念,也試着看見他背後那個時代、那段路、那個可能沒有被好好說完的流亡故事。
五、從「中國」到「香港」:流亡對象的轉移
我在《我城存歿》與《香港已死?》裏提出一個沉痛的判斷:香港已死。這不是危言聳聽,而是一個哲學診斷。我說「香港已死」,指的是那個讓我們得以安身立命的「我城」— 一個以自由、法治、多元為核心的城市精神 — 在制度、文化與精神三重層次上被系統性摧毀。
這樣的說法與唐君毅的「花果飄零」頗為相似,卻又不同。對唐君毅而言,「花果飄零」的是整個「中華民族」,而靈根則植於儒家傳統;對我而言,「死亡」的是一個具體城市 — Hong Kong — 而我試圖守護與再造的,是一種香港式的自由精神與市民文化。
當我宣稱「香港已死」,同時又反覆問:「我們還有家嗎?」這就是流亡者的根本矛盾:我們知道那個曾經的家園已無法回去,卻仍然無法放棄對它的哀悼與記憶。在這個意義上,我與唐君毅、牟宗三等人是相通的:他們為「中國」招魂,我則為「香港」寫墓誌銘。只是,我所哀悼的對象不再是一個抽象的文化單位,而是極為具體的街道、山城、校園與廣場,是一代人在雨傘運動與反修例運動中共同體驗過的「我城」。
六、後來者的流亡反省:余英時與趙越勝
身處流亡,我也常想起兩位與我有某種精神親近的學者:余英時與趙越勝。
余英時在〈從鄉間到流亡,我走過的路〉裏回憶自己從北平到香港、再到美國的經歷,說那是一段「流亡期間」,並明白地稱自己為「海外的流亡者」。這種坦率對我們這一代極有啟發:他沒有把自己包裝成「旅居學者」或「海外華人」,而是承認自己的離開與時代災難密切相關。
在普林斯頓,他多次參與、扶持來自中國的流亡學者與民運人士,並在思想上思考「流亡知識人」的角色。他關心的不再只是儒家,而是整個中國現代思想如何在專制與流亡中掙扎。對我而言,余英時代表了一種歷史化的流亡自覺:流亡不是單一世代的悲劇,而是現代中國知識人命運的一部分。
趙越勝則是另一種風格的流亡哲學人。他在 1989 年後移居法國,在《荒誕的世界與反叛的智者》等書中,將流亡、反抗與荒誕連在一起看。他問:流亡了的中文寫作者還有沒有可能留下思想成果?當語言失去社會現場,當讀者與作者被暴力隔開,哲學與文學是否註定走向枯竭?
他從拉波哀西到加繆,一路追索「不合作」與「反叛」的倫理,把流亡理解為一種拒絕 — 拒絕遺忘、拒絕屈服、拒絕加入謊言。在他的筆下,流亡不再只是對祖國的哀傷,而是對極權的持續抵抗。
這兩位學者的書寫,對我重新理解自己的流亡身份極為重要:一方面,他們提醒我,自己並非孤例,而是二十世紀以降華語思想中一條長線上的一個點;另一方面,他們也逼我承認:流亡不是「暫時的」,而可能是一輩子的命運,必須在其中找到持續思考與創作的方式。
七、我與「三代流亡哲學學者」
在《滄海橫流要此身》的講座裏,我曾用「三代流亡哲學學者」這個說法來整理自己的脈絡:
第一代,是五四以來在戰亂與政權更替中流離失所的學人,代表人物就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錢穆這一批。他們從大陸南來香港、再赴台灣或西方,在「花果飄零」的語境中重建儒學與中國哲學。
第二代,是戰後在白色恐怖、戒嚴體制與冷戰結構中穿梭的學者,包括台灣、本地及海外華人學界的一整代人。他們或許沒有明言「流亡」,但實際上生活於國家暴力的陰影下,知識人的空間隨時可能被收緊。許多香港與台灣的哲學人,常年在紅線邊緣自我審查,在「可以說到哪裏」與「不可以說甚麼」之間小心拿捏,其實也是一種內在化的流亡。
第三代,就是我們這一批香港出身或長年在香港教書的哲學人:我們在英殖的餘緒與「一國兩制」的幻象中成長,在短暫的自由高峰中教書、寫作,然後在國安法與白色恐怖降臨時被迫離開。從法理上看,我們是移民、是申請庇護者;從精神上看,我們是從一個被宣告死亡的城市撤離出來的「遺民」。
當我稱自己為「香港遺民與流亡哲學人」時,我既是在承繼前兩代的命名,也是在指出一個斷裂:我已經不再能簡單地說自己是「中國文化人」,我的第一身份是「香港人」,而「中國」在我這一生裏更多時候是壓力與暴力的來源。唐、牟那一代所談的「中國」,對他們而言仍然是可盼、可戀、可再造的對象;對我們而言,「中國」更多是需要保持警惕、保持距離、甚至必須公開抵抗的力量。
因此,我在談流亡時,很難再用「靈根自植於中國文化」來安慰自己。對我而言,「根」更多是具體的人與事,是在中大山城一起工作的同事、學生,雨傘運動中在連儂牆貼貼紙的年輕人;反修例運動中受傷、被捕、流亡的無名者;仍在監獄的黎智英、鄒幸彤、戴耀廷、何桂藍等等拒絕屈服的香港人,成為我此刻在異鄉回想時最難割捨的根系。
如果說我還相信「靈根自植」,那麼這個靈根應該植於「誠實面對自己與時代」的良知之中,而不必一定捆綁在某一種固定的「中國」想像上。這也是為甚麼,我會在書裏反覆強調:做一個「人」、講真話、明辨真相與假相、活在真相之中,是哲學人的最低責任。這樣的「靈根」,或許比任何單一民族、單一文化的認同更堅韌,也更不容易被政權收編。
八、流亡哲學人的幾個問題意識
作為一個仍在流亡路上的哲學人,我對流亡的反省,目前大致集中在幾個問題上:
(一)家與無家
在《香港已死?》中,我有一章叫〈我們還有家嗎?家與流亡的哲學反思〉。這不是修辭,而是切身之問。流亡者體驗到的是一種雙重無家:物理上的房子可能還在,但已經無法安全回去;精神上的家園 — 香港那個曾經開放、多元與自由的「我城」— 則在制度與文化清洗中迅速崩塌。
在現象學語境裏,「家」不只是住所,而是整個「在世」結構的基礎:語言環境、日常習慣、熟悉的街景與人際網絡,構成一個世界的背景。流亡者被迫離開的,往往是整個世界,而不是一個地址。當你在異國超市聽見偶然飄來的一句粵語、在街角看到一面「香港人社群」的小貼紙,那種瞬間的鼻酸與心悸,其實就是「家」在斷裂後仍不肯完全消失的證據。
我從海德格學到的是:我們無法退回一個純粹抽象的「自我」,每個「此在」總是在某個世界中被投擲。流亡就是被迫改寫這個「投擲」— 原本我們以為自己會在香港終老,卻在晚年被丟到另一個語言與文化環境裏。這樣的斷裂必然伴隨孤獨、憤怒與無助,但也逼我們重新問:當一切熟悉的支撐都不在時,「我」還剩下甚麼?
(二)希望
在《香港已死?》中,我談了希望。流亡者最容易陷入的,是雙重極端:不是絕望到甚麼都不做,就是自欺到相信「一切很快會變好」。這兩種態度,從哲學角度看都過於草率。
牟宗三那代前輩,對未來有一種堅定的信心:他們相信中國終有一天會走向民主與自由,相信儒家在世界文化上仍有角色。我不能說他們錯了,但二十一世紀中國與香港的發展,讓我們的樂觀空間極度收縮。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更願意把「希望」理解為一種實踐中的堅持:不是對宏大歷史結果的樂觀,而是在具體行動中保留對真理與正義的忠誠。書寫、教學、見證、拒絕說謊 — 這些微小而持續的行為,就是流亡者唯一可負擔得起的希望政治。希望不再是對某個遙遠未來的美化,而是每天仍願意寫下真話、向學生說清是非、記住被消失的名字。
(三)哲學人的責任
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錢穆給我們留下了一種典範:哲學人不是躲在象牙塔裏的人,而是要在時代的滄海橫流中承擔某種公共責任。余英時、趙越勝在流亡中持續書寫與發聲,是這一典範的延續。
我在《香港已死?》裏明說:哲學必須走出象牙塔,特別是在強權壓境的時代,哲學人不能只在書齋裏談意義與存在,而不去面對具體的不義與暴力。這不是要每個哲學人都去做運動領袖,而是至少要拒絕為暴政粉飾、拒絕在課堂與文字中協助麻醉青年。在香港的最後幾年,我愈來愈強烈地感到:如果哲學只剩下對概念的純粹把玩,而不敢觸碰現實的暴力,那麼哲學本身也已被閹割。
流亡加重了這個責任。當我們已經到了相對安全的地方,身上就多了一層「見證人」的角色:如果連我們也沉默,那麼那些仍在風暴中心的人,就更加孤立無援。哲學人的文字,當然無法立刻改變政權,但至少可以保留一條不屈從的語言脈絡,讓未來的人知道:在這個荒謬年代,仍然有人拒絕說假話。
九、結語:在前輩與後來者之間自處
寫到這裏,我知道自己既不配也不願自稱為「新牟宗三」或「新唐君毅」。我只是一個在香港長大、在中大教書、在攝相與篆刻之間走路的哲學人,偶然撞上時代的洪流,被迫在晚年流亡。
然而,流亡也讓我更清楚看見自己所屬的長線:前有牟宗三先生,在「虛偽時代」裏以儒家與康德之對話回應現代性;唐君毅前輩,以「花果飄零/靈根自植」為流亡一代尋找精神依靠;後有余英時、趙越勝等學者,將流亡視為歷史與荒誕中的反叛位置;再到我們這批香港流亡哲學人,用「香港已死」與「家與無家」的語言,嘗試為一座被摧毀的城市立傳。
如果說這幾代人之間有一條共同的線,那就是:在無家可歸的世界裏,仍然不放棄思考與說話。哲學人對流亡的反省,最終不是為了美化自己的命運,而是要提醒所有身處壓迫與流離的人 — 哪怕世界已經荒謬至極,我們仍然可以選擇不說謊,不背棄良知,不放棄對真理與自由的渴望。
在這個意義上,牟宗三並非只是歷史上的哲學大師,而是一個仍在流亡者心中說話的同行者。當我在異鄉小房間裏寫下這些句子時,我知道,我並不孤單。那些在香港新亞、在普林斯頓、在巴黎、在倫敦、在台北的流亡哲學人,都在同一片暗夜裏摸索着前行。這種「同行」本身,就是流亡哲學最深的慰藉,也是我在老年流亡歲月裏仍願意提筆的最終理由。
張燦輝
流亡哲學人
《橫流集》專欄系列之前其他文章,請到《追新聞》網站瀏覽:https://thechasernews.co.uk/t/橫流集/
相關新聞
- 2026 年 01 月 01
- 2026 年 01 月 02
- 2026 年 01 月 29
- 2026 年 01 月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