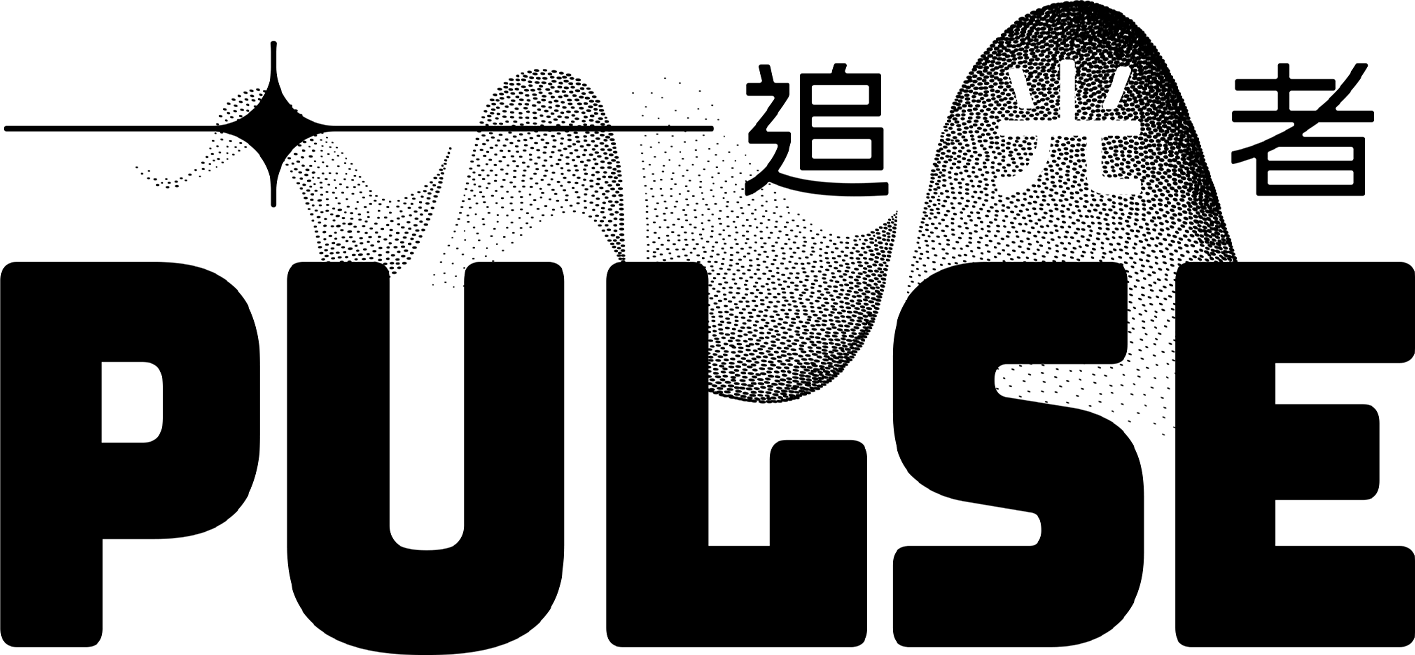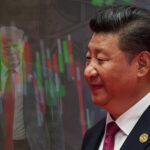香港中文大學學生關靖豐,早前因就宏福苑大火發起聯署並提出「四大訴求」,其後被警方國安處拘捕。案件未有發展至起訴階段,校方已隨即展開紀律程序,最後裁定部份原有指控不成立,卻以關靖豐在聆訊中「不禮貌與不尊重」以及被指洩露傳召內容為由,記兩次大過。連同之前因拒絕接種疫苗以及隨街張貼「六四」貼紙而留有刑事紀錄的處分,關靖豐最終因累積大過達到終止學籍門檻,畢業前夕被中大踢出校。
事件引發不少爭議。有校友與公眾人士認為,中大的處理方式欠缺公允,於是發起聯署要求校方重新檢視決定。關靖豐亦表示,將循校內渠道提出上訴。這場上訴的意義,或許並不僅在於關靖豐能否取回公道,更關乎外界是否有機會對校方紀律決定的程序基礎進行更嚴格的檢視。
問題的核心,未必只是校規是否被遵守,而是校規的運用是否符合「程序正義」(procedural justice)的精神。程序合規(procedural compliance)並不必然等同於程序公正。當紀律程序在尚未出現具體刑事起訴的情況下啟動,而最終裁決又落在聆訊態度與保密規定等行為的判斷上,我們便有必要進一步討論:程序的啟動基礎是否清晰、指控是否具體、處分是否符合比例原則(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
兩次紀律聆訊在程序基礎存差異
根據公開資料顯示,關靖豐2022年6月4日因在旺角張貼「真嘢唔怕講」貼紙,其後被裁定刑事毀壞罪成並判罰款。隨後,校方才就相關行為召開紀律聆訊,並作出停學及記過處分。換言之,上一次校內紀律程序的啟動,是在法院已就相關行為作出司法確認之後進行。
然而,這一次的情況卻有所不同。就宏福苑聯署一事,關靖豐雖曾被警方拘捕,但案件並未發展至起訴階段。在尚未有正式檢控或司法定罪的情況下,校方已展開紀律程序。更重要的是,最終部分原有指控未獲成立,而處分理由則轉為「不禮貌」、「洩露傳召內容」等行為判斷。
這種時序差異本身,並不必然代表程序不合規。現行校內紀律機制,亦未必要求必須等待法院定罪後才可啟動。然而,在程序正義的框架下,仍有值得追問之處:當紀律程序在缺乏司法確認的情況下啟動,其啟動基礎是否足夠清晰?指控是否具體明確?以及在最終裁決轉向態度與程序性行為時,是否出現焦點偏移?
若上一次的處理建立於已被司法確立的違法事實之上,而這一次則在尚未確立實質違規前即啟動聆訊,那麼兩次紀律處理在程序基礎上的差異,便成為評估其是否符合程序正當性與比例原則的重要切入點。
指控範圍模糊令當事人感困惑
更重要的是,當紀律程序在尚未有明確司法結論、甚至未有具體違規事實被清楚指明的情況下啟動,對當事人而言,本身便可能構成一種高度不確定的制度壓力。若指控範圍模糊或理由未被具體交代,當事人自然可能對聆訊的公平性產生不信任,甚至對制度是否中立存在質疑。
程序正義理論一再強調,制度的正當性不僅取決於最終裁決,更取決於當事人對程序是否公平的主觀感知(perceived procedural fairness)。若當事人認為自己被傳召的基礎並不清楚,或無法理解具體違規所在,其情緒反應便不一定只是單純的態度問題,而可能反映對程序信任的動搖。
根據傳媒報道,關靖豐在回覆電郵中曾形容該委員會為「袋鼠法庭」(Kangaroo Panel,意指不公正的審判),甚至稱之為一種「恥辱」(disgrace)。難道當權者覺得這兩句說話「難聽過粗口」?這些言辭固然尖銳,但若放在對程序公正性產生疑慮的背景下理解,便未必只是單純的言語失當,而可能是對制度正當性提出質疑的情緒表達。因此,當制度信任出現裂痕,聆訊過程中的語氣與態度,便難以完全脫離這種心理與結構背景而被孤立評價。
聆訊焦點為轉向情緒反應須商榷
更值得討論的是,若紀律程序本身的啟動基礎存在爭議,而最終處分卻主要落在關靖豐在聆訊中的情緒或言辭表現之上,那麼問題便不再只是尊重或禮貌問題。關鍵在於,學生紀律委員會究竟是在處理關靖豐因宏福苑大火聯署一事,還是在處理他對聆訊的不滿與質疑?當焦點由實質行為轉向對程序本身的反應時,程序與結果之間的關係便值得重新檢視。
在法律社會學中,這種情況常被理解為懲罰具有「表達性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 of punishment)。懲罰不只是為了糾正錯誤或排除風險,它同時也是在向外界傳遞訊息:哪些行為不能接受,哪些界線不可跨越。當制度對聆訊中的態度作出嚴厲回應,其意義便不只限於這一宗個案,而是在重申制度的權威與邊界。
若再結合時間因素,在關靖豐臨近完成學業之際作出終止學籍決定,這種處分便難以僅以風險預防加以理解。從風險治理角度而言,他本已接近離校,其對校園秩序的實際影響有限;然而,處分仍然落實,制度所完成的,便更接近一種邊界宣示(norm signalling)。它不僅是在管理風險,更是在重申制度權威。簡而言之,就是要向外界產生某種警示作用。
值得檢討制度承受質疑能力
至於校方指洩露傳召內容可能損害校譽的說法,就便難以服眾。若校譽如此脆弱,以至於一場紀律聆訊的內容被公開便足以動搖聲譽,我們或許更應反問:究竟是學生的言辭削弱了大學的形象,還是紀律機制本身的運作方式,正在改寫公眾對大學的理解?若「校譽」成為處分理由,那麼真正值得檢視的,或許不只是學生的態度,而是制度本身對質疑的承受能力。
若將視野稍為拉遠,問題便不只停留在個案層面,而涉及制度目標的轉向。羅爾斯(John Rawls)在《正義論》中指出,在「不完全程序正義」(imperfect procedural justice)之下,即使程序設計合理,結果亦未必符合實質公正。程序並非價值中立,它總是服務於某種制度目標;當制度目標由保障公共理性(public reason)轉向維持秩序與降低不確定性,程序的功能自然隨之改變。
在國安法所塑造的泛政治安全環境下,香港高等院校難以與整體治理語境切割,甚至逐步嵌入更廣泛的監管與風險管理體系之中。「維穩」成為優先考慮因素,風險降低(risk mitigation)凌駕於公共理性與教育使命之上。但重點已不再是處理分歧,而是盡早劃清界線,把可能帶來爭議的人或事清走。
學生因公共議題行動而被拘捕,大學首先啟動紀律程序,而非明確提供支援與保障,這種處理次序本身,已令人質疑制度目標是否正在轉向。大學究竟將學生視為需要引導與保護的成員,還是需要管理與切割的風險來源,差別正在於此。若大學運作邏輯皆以國安維穩為前提,紀律程序與開除學籍便容易被外界理解為要學生噤聲的「武器」。或許沒有人會承認要震懾誰,但制度所傳遞的訊號,卻難免讓人產生寒意。大學是否正淪為維穩機器的一環,這或許正是關靖豐事件引起強烈回響的深層原因之一。
相關新聞
- 2026 年 02 月 06
- 2026 年 01 月 16
- 2026 年 02 月 04
- 2026 年 01 月 23
- 2026 年 01 月 09
- 2026 年 02 月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