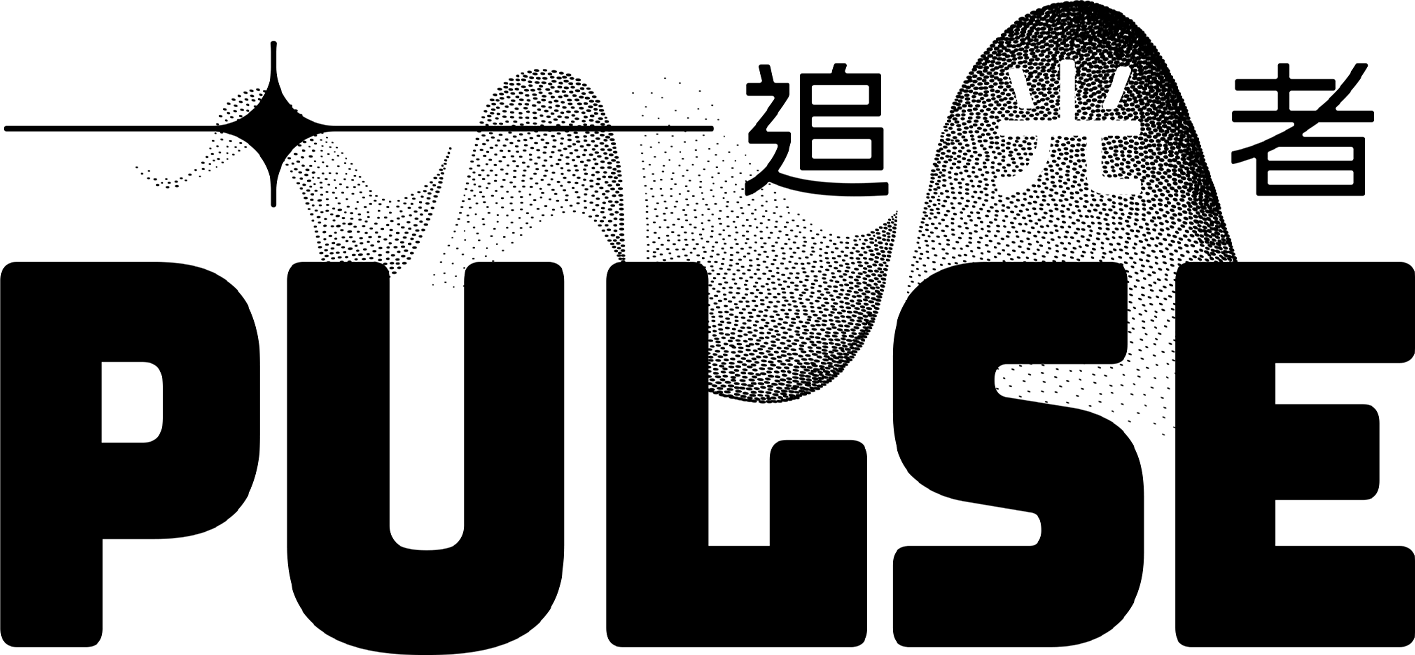(筆者按:近日拜讀陳文敏教授在綠豆破土的「雙軌國家」,以及程翔先生在追光者香港首席法官張舉能的幾篇文章。讀後不勝唏噓和悲憤。覺得需要將心中感受書寫出來。文中不少論點是根據陳文敏和程翔的文章引發出來,在此感謝兩位先生的論述。)
「最嚴重的暴行莫過於在法律保護下以正義的名義實施的暴行。」
(孟德斯鳩)
引言:法袍下的道德深淵
二零二六年一月,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在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義正詞嚴地宣稱「法律平等適用於每個人,無懼無偏」,並高調譴責國際社會要求釋放黎智英的呼聲是「干預司法獨立」。他慷慨激昂地說:「我不會願意生活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也不會願意成為這樣一個社會的首席法官。」
這番話聽來正義凜然,底氣十足。然而張舉能的實際所為,與他的高調宣言形成了何等諷刺的對照。香港司法在他任內經歷的系統性崩壞,法治如何在他的默許甚至配合下淪為威權統治的工具,這一切都迫使我們正視一個令人戰慄的事實:張舉能正在香港重演一九六一年克雷默執導的電影《紐倫堡大審判》(Judgement at Nuremberg) 中揚寧法官的悲劇。揚寧是一個備受尊敬的法律權威,卻在極權體制下成為司法謀殺的共謀者。(儘管楊寧是電影中杜撰的角色,但相信在納粹年代肯定有不少真實的楊寧法官存在。)
在我此前的文章〈三種邪惡的面貌:從艾希曼、戈林到揚寧法官的道德哲學反思〉中,我探討了納粹時期三種不同類型的邪惡。艾希曼代表「平庸之惡」,是無思的官僚執行者;戈林代表「權力之惡」,是清醒而貪婪的權力追逐者;揚寧則代表第三種更為幽微的邪惡,是知識分子在極權體制下的道德投降與自我欺騙。如今,我提出第四種邪惡的面貌: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提到那些審判黎智英的法官們,張舉能同樣是屬於這第四種邪惡。這種惡是揚寧之惡在當代香港的變體與延續,卻又有其獨特的陰險之處。張舉能不僅重蹈揚寧的覆轍,更是在全球關注下、在國際法治社會的批評聲中,選擇將香港百年法治傳統親手埋葬。他的罪責比揚寧更重,因為他無法聲稱自己「不知道」——歷史的前車之鑑就在眼前,而他選擇視而不見。
一:揚寧的幽靈——知識分子的道德投降
一九六一年的電影《紐倫堡大審判》講述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故事。揚寧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學教授和前司法部長,在納粹時期從一個捍衛法治的法官逐漸墮落為司法謀殺的共犯。揚寧不是狂熱的納粹黨員,他甚至對納粹的某些做法有所保留,但他選擇了留在體制內,選擇了妥協,以「維護司法秩序」的名義簽署那些將無辜者送進集中營的判決書。
揚寧的悲劇在於他是一個有良知的人,但他的良知被「現實考量」所壓制。他說服自己留在體制內可以「做一些好事」,「減少傷害」,「維持法治的形式」。他用一套精緻的自我欺騙話術為自己的道德投降辯護。然而正如電影中美國法官海伍德所指出的,當揚寧簽署第一份不公正的判決書時,他就已經犯下了他全部的罪行,因為那一刻他選擇了放棄作為法官最根本的職責:守護正義。
揚寧的邪惡不同於艾希曼的無思,也不同於戈林的貪婪。揚寧的邪惡是一種「有教養的邪惡」,是知識分子在面對極權時的懦弱和自欺。他完全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他知道那些判決是不公正的,也知道無辜者會因此喪命,但他說服自己這是「必要的犧牲」,是「維護大局穩定」的代價。這種邪惡之所以特別可怕,是因為它穿着文明的外衣。揚寧引經據典,條理分明,他的判決書寫得文采斐然,法理精深,但正是這種「專業性」使得暴行獲得了合法性的外觀。當法官成為壓迫機器的一部分,司法成為政治迫害的工具,法律本身就變成了最大的謊言。
揚寧最終在法庭上承認了自己的罪行,說:「我知道我們做的是錯的。」這個承認來得太晚,但至少他恢復了某種道德清醒。然而張舉能至今還在用冠冕堂皇的辭令為自己辯護,仍在假裝香港的司法是「獨立」的,扮演法治守護者的角色。這種自欺欺人比揚寧更加可鄙。
二:雙軌國家——香港法治的結構性瓦解
要理解張舉能之惡的深層結構,我們必須引入德國律師弗蘭克爾在其經典著作《雙軌國家》中提出的分析框架。陳文敏教授最近在《破土》發表的文章正是以這一理論來剖析香港法治的當下處境。
弗蘭克爾在納粹上台前長期為工會與勞工辯護,親身體驗司法制度如何在政治壓力下逐步失去獨立。他觀察到在一般民事或商事糾紛中,法院仍依據既有法律作出判決,但一旦案件涉及政權或黨的利益,司法便變得扭曲,行政部門可隨時干預或拒不執行判決,法律的適用亦會因政治而變得選擇性,正義不再普遍實現。弗蘭克爾其後帶着未完成的手稿流亡海外,最終於一九四一年完成了這部名著。
在書中,弗蘭克爾以深刻的洞察分析納粹德國的法律結構,提出「雙軌國家理論」。他指出納粹政權下同時存在兩種國家形態:「規範國」仍依循既有法律與行政程序運作,「特權國」則以黨的命令與領袖意志為最高原則,凌駕於法律之上。這兩種體制並存,使國家一方面保留法律外觀,另一方面卻由政治暴力與任意權力主宰。弗蘭克爾認為這樣的制度顯示法律並非自然崩潰,而是被權力有意識地分化與操控。當特權國不斷擴張時,規範國的空間便會逐漸被侵蝕,最終導致整個法治秩序崩解。
陳文敏教授指出這套理論解釋了不少現代威權政體的運作。傳統的威權政體以武力鎮壓來統治國家,在高度集權的政體中不容任何異見,亦不會容忍任何獨立的司法體系。現代的威權政體一方面承傳傳統威權政府的特色,打擊異己,壓制言論,禁止任何挑戰政府的批評,但另一方面又意識到維持一個獨立的司法形象既可促進經貿發展,亦可因法院的認可而增強其管治的合法性。法院提出的理據更可以為嚴苛的管治提供文明的藉口,將高壓的管治合理化,法院的判決也成為反駁內外批評聲音的依靠。
於是在經濟或非敏感的領域,即弗蘭克爾所稱的「規範國」領域,司法保持獨立,法治獲得彰顯。但在政治敏感的領域,即弗蘭克爾所稱的「特權國」領域,嚴苛的法律令法院處處受到制肘。法院一旦偏離政權的意願,政權會隨即介入推翻法院的判決。陳文敏教授舉出了鮮明的例證:在梁游宣誓案中,人大常委會在法院判案前夕以釋法指示法院該如何判決;當各級法院一致批准黎智英延聘海外大律師作代表律師時,政府先後以釋法和修例推翻法院的判決。
香港「雙軌國家」的具體表現觸目驚心。在普通的刑事案件中香港依然保留陪審團制度,但在《國安法》案件中律政司可以發出證書取消陪審團,唐英傑案、黎智英案、四十七人案全部沒有陪審團,被告在政治案件中被剝奪了由同儕審判的基本權利,命運完全交由指定法官裁決。在普通刑事案件中保釋是原則、羈押是例外,但在《國安法》案件中這個原則被顛倒,黎智英被拒絕保釋超過四年,四十七人案的被告在審訊前已被羈押超過一千日,這種長期的審前羈押本身就是一種未經定罪的懲罰。在文明的法治社會刑法不應具有追溯力,但《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修改了假釋規定並明確賦予追溯效力,違反了《人權法案》的基本原則。《國安法》第十四條明確規定國安委的決定不受司法覆核,在國家安全的名義下行政權力可以完全凌駕於司法之上,法院被剝奪了監督政府的基本功能。當終審法院判決批准黎智英聘請英國御用大律師時,行政長官李家超立即提請人大釋法推翻終審法院的判決,清楚顯示在政治案件中終審法院的「終審權」不過是一紙空文。
陳文敏教授更尖銳地指出,在「特權國」的領域內法院只能為政權搖旗吶喊。在強大的政治壓力和嚴苛及模糊的法律條文下,荒謬的檢控、脆弱的檢控理據、單薄的證據皆被法院照單全收並加以合理化。在高舉國家安全的大旗下法律的合理性已不再受質疑或挑戰,法律的解釋和應用變得機械化。法院在解釋煽動罪時不惜離棄整個普通法世界對煽動暴力或破壞公共秩序的要求,或將跟從《基本法》程序的初選界定為非法行為,甚至容讓控方在支聯會案中提出一直無法說清楚的非法行為。法院開始遺忘了維護基本人權和自由的責任,亦不會問被控的行為如何嚴重危害國家安全。
檢控由最初涉及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漸漸轉移至針對言論和思想的政治檢控。法院依法定罪,程序是公平的,審訊是公開的。法院不是立法或制定政策者,法院必須跟從法律判案,但在解釋及應用法律時法院仍然有一定的空間。可惜在「特權國」的領域內,法律是否合理合憲、定罪是否符合公義都變成政治問題,不能以此批評司法不公、法治不張。法治只淪為程序公義,為荒謬的定罪塗上合法的脂粉。
陳文敏教授總結道:雙軌國家的理論解釋了為何在同一國家法治和極權可以並存。雖然有評論者指出弗蘭克爾的二元劃分過於簡化,忽略了兩軌國家形式之間的互滲和互動地帶,亦沒有充分探討從法治走向威權的過程中法院所扮演的角色和轉變,但它揭示出即使在形式上維持法律框架的體制之中法律也可能淪為權力的附庸,這一警示至今仍深具現實意義,也對瞭解香港法治的處境和變化有不少啟示。
在這個「雙軌國家」中張舉能扮演了什麼角色?他是這個體制的門面,是「規範國」的象徵,他的存在使得「特權國」的暴行獲得了合法性的掩護。每當他在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宣稱香港的司法是獨立的,他就是在為這個壓迫體制背書。
三:程翔的控訴——張舉能的瀆職罪
資深新聞工作者程翔近日在《追光者》發表系列文章,以「張舉能的瀆職罪」為題從多個層面剖析張舉能的失職與失德。這些控訴有理有據,值得我們認真審視。
程翔指出張舉能熱衷於接受中共的統戰,涉嫌違反了香港《法官行為指引》。自二零二一年出任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以來,張舉能五年內五次率團訪問大陸,頻率遠超其前任。李國能十年間僅有兩次官式訪問,馬道立十年間共有三次,張舉能的頻密程度顯而易見。
這種頻密的「交流」為何成問題?《法官行為指引》明確要求法官應避免加入任何政治組織或與之有聯繫或參與政治活動。該指引強調法官不僅要事實上做到不偏不倚,還要讓外界相信法官是不偏不倚的,公義必須是「有目共睹」的。任何對中共統戰手法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這種「交流」與「訪問」是統戰工作的第一步,統戰的最終目的是改變被統戰者的思想意識形態,使之成為中共的支持者或同路人。
程翔更進一步指出,最令人擔心的是法官把中共的意識形態「內化」,因為這意味着法官可以不在中共的直接壓力或指示下,自動自覺地作出合乎中共心意的判決。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任石榮教授和陳秀慧教授的研究論文也證實了這一觀察。他們比較了三位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雄辯領導力」,結論是李國能採取「大膽而主動」的方式將香港法律體系與更廣泛的普通法世界聯繫起來,馬道立致力於就法治問題與公眾溝通,而張舉能的做法則「比前任更妥協和迴避」。兩位法律學者的評價客觀但結論清晰:張舉能對中共採取了更順從的態度。他對西方的批評可以嗤之以鼻,但對中共這個真正能主宰香港命運的權貴卻自覺或不自覺地配合,這是最大的向權貴屈服。
程翔再指出張舉能未能履行其維護香港憲政秩序的責任。《基本法》第二條明確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然而在張舉能任內這些權力一再被侵蝕:人大釋法推翻終審法院判決,國安委的決定不受司法覆核,《國安法》指定法官制度架空了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面對這些侵蝕張舉能保持沉默,更糟糕的是他用冠冕堂皇的辭令為這些侵蝕辯護。當國際社會質疑香港的司法獨立時他跳出來譴責「外國干預」,但當中共三個中央級部門在黎智英案未審結前不斷發表聲明定其有罪時他卻一言不發。這種選擇性的「維護司法獨立」恰恰暴露了他的虛偽。正如程翔所問:「對這些『外部』勢力的干擾,張舉能敢斥責嗎?在港英時代,傳媒這樣做是要被控『妨礙司法公正』的。」
《基本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繼續有效,通過香港特區的法律予以實施,這意味着香港法院有責任確保人權公約得到遵守。然而在《國安法》案件中我們看到的是人權保障的全面倒退:未經審訊的長期羈押、剝奪陪審團審判的權利、限制被告選擇律師的自由、對言論自由的寒蟬效應。作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有責任也有權力挑戰這些違反人權的做法,但他選擇了沉默,選擇了配合,選擇了將「國家安全」置於人權之上。這不僅是對《基本法》的背叛,更是對法官根本職責的背棄。
四:言行不一的虛偽——張舉能的雙重標準
張舉能在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的講話堪稱虛偽的典範。他宣稱「沒有人能凌駕法律之上,不會因個人的地位、職業、職銜、政治聯繫、個人信仰或信念、聲望、財富、人脈網絡或其他特點而有差別」,這話說得漂亮,但現實是黎智英被拒絕保釋超過四年,而建制派人士涉及同類案件卻可以獲得寬大處理;民主派人士因組織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最高被判十年監禁,而真正操縱選舉、破壞民主制度的人卻高居廟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話說給誰聽?
張舉能將國際社會對香港法官的制裁威脅比作「貪腐賄賂」,聲稱這是「破壞公義的手段」。但他為何不提中共對香港法官的「威脅」?為何不提那些拒絕配合的法官所面臨的壓力?為何不提國安公署、中聯辦、港澳辦在案件未審結前的公開表態?如果說國際社會的批評是「威脅」,那麼中共的統戰和施壓又是什麼?張舉能對前者義憤填膺對後者卻噤若寒蟬,這不是雙重標準是什麼?
張舉能說「真誠致力維護法治的人必然同時支持法庭按照確立的法律程序執行司法工作不受干預」,但他所謂的「確立的法律程序」是什麼?是《國安法》凌空降落繞過香港立法程序的「程序」?是人大釋法推翻終審法院判決的「程序」?是國安委決定不受司法覆核的「程序」?這些「程序」有哪一項是香港法律傳統所「確立」的?張舉能所維護的不是法治,而是披着法律外衣的威權統治。
五:握實法治傳統的雙手——終結者的自白
我在文章開首說張舉能「將香港法治傳統在他手中握實」。這句話需要解釋:他握實的目的不是為了守護,而是為了扼殺。
香港法治傳統是什麼?它是一套經過百年積累、與國際普通法世界接軌的制度和價值。它是司法獨立,法官不受政治干預只根據法律和證據裁判。它是正當程序,任何人被定罪前都有權獲得公正審訊、有權聘請律師、有權由陪審團審判。它是人身自由,未經定罪不得長期羈押,保釋是原則而非例外。它是言論自由,即使是批評政府的言論也受到法律保護。它是無罪推定,控方必須證明有罪而非被告證明無罪。這套傳統是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根基,它使香港成為亞洲的國際金融中心,令到香港成為不同於中國大陸的獨特存在,讓世界知道香港人享有大陸人民所沒有的自由和保障。
在張舉能任內這套傳統正在被系統性地摧毀。陪審團制度被架空,在最需要它的政治案件中它被取消了。正當程序被破壞,被告被剝奪選擇律師的自由,人大釋法推翻終審判決。人身自由被侵蝕,政治犯被長期羈押,保釋變成例外而非原則。言論自由被窒息,記者被判刑,媒體被關閉,自我審查成為常態。無罪推定被顛倒,在國安案件中被告必須證明自己「不會危害國家安全」才能獲得保釋。這一切都發生在張舉能的眼皮底下,發生在他的默許甚至配合之下。他不是旁觀者,他是共犯。
當他在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宣稱香港司法「獨立」、「公正」時,他是在為這套壓迫體制背書,是在為這套虛假的法治塗脂抹粉,是在欺騙國際社會,更是在侮辱那些因捍衛真正法治而身陷囹圄的香港人。
六:歷史的審判——張舉能無法逃脫的責任
讓我們回到揚寧的故事。在《紐倫堡大審判》的結尾揚寧向海伍德法官承認:「我知道我們做的是錯的。」這個承認是揚寧恢復道德清醒的時刻,他終於放棄了那套精緻的自我欺騙話術承認了自己的罪行。但這個承認來得太晚,數百萬人已經死去,一個文明已經被摧毀,揚寧的懺悔無法挽回那些生命無法彌補那些傷害。他被判處終身監禁死在獄中。
海伍德法官在判決書中說了一句至關重要的話:「當你簽署第一份不公正的判決書時,你就已經犯下了你全部的罪行。」這句話的意思是一旦法官開始與不義妥協他就已經喪失了作為法官的資格,此後的所有判決無論看起來多麼「專業」都已經被那第一次妥協所玷污。
張舉能的「第一份不公正的判決書」是什麼時候簽署的?是他第一次批准國安法案件不設陪審團的時候?是他第一次默許長期審前羈押的時候?是他第一次對人大釋法保持沉默的時候?無論確切的時間點是什麼有一點是清楚的:張舉能已經越過了那條線。他已經不再是一個公正的法官而是威權統治的幫兇,他的每一次冠冕堂皇的演講都是對法治的嘲弄,他的每一次「維護司法獨立」的聲明都是在往傷口上撒鹽。
有朝一日當香港重獲自由、當真正的法治得以恢復,張舉能必將面對歷史的審判。屆時他無法聲稱自己「不知道」,整個世界都在看着香港發生的一切。他無法聲稱自己「無能為力」,作為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他擁有捍衛法治的權力和責任。他不可能聲稱自己「只是在執行法律」,正是這種辯護被紐倫堡審判所拒絕。張舉能必須為他的選擇負責。他選擇了妥協,配合,將個人的安逸和地位置於公義之上。這個選擇定義了他是誰。
結語:第四種邪惡的警示
我在文章開首提出張舉能代表了「第四種邪惡」,是揚寧之惡在當代的變體。張舉能是虔誠基督徒、哈佛法學碩士、資深法官,他的判決書寫得文采斐然,這使他的邪惡披上了教養的外衣。他可能真的相信自己是在「維護法治」,真的相信香港司法是「獨立」的,這種自我欺騙使他的良知得以安睡。但他對西方批評的慷慨激昂與對中共統戰的甘之如飴形成鮮明對照,暴露了他選擇性的道德標準。正是因為他的配合,威權統治獲得了合法性的外衣,壓迫獲得了「法律」的名義。
這種邪惡之所以特別可怕,是因為它使抵抗變得更加困難。如果香港的司法是赤裸裸的政治審判,國際社會可能更容易介入,但因為有張舉能這樣的「門面」,有那些寫得像模像樣的判決書,有那些「程序正義」的假象,壓迫就變得更加隱蔽更加難以被揭露。張舉能的存在是威權統治的最佳護身符,他是揚寧的當代化身,是知識分子道德投降的活標本,是法治如何死於「法律人」之手的鮮明例證。
歷史將記住張舉能,但不會以他自詡的方式。他將作為法治的掘墓人、威權的幫兇被銘記於史冊。香港法治的最後一縷餘暉正在熄滅,我們這一代流亡者只能在異鄉遙望故土,無數政治犯在牢獄中消耗青春,而這一切都是在張舉能的眼皮底下、在他的默許和配合下發生的。
他的雙手握實了香港法治傳統,然後把它扼殺了。這就是第四種邪惡的面貌:一個本應守護正義的人成為了正義的終結者。
張燦輝
流亡哲學人
二〇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相關新聞
- 2026 年 01 月 22
- 2026 年 01 月 22
- 2026 年 01 月 01
- 2026 年 01 月 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