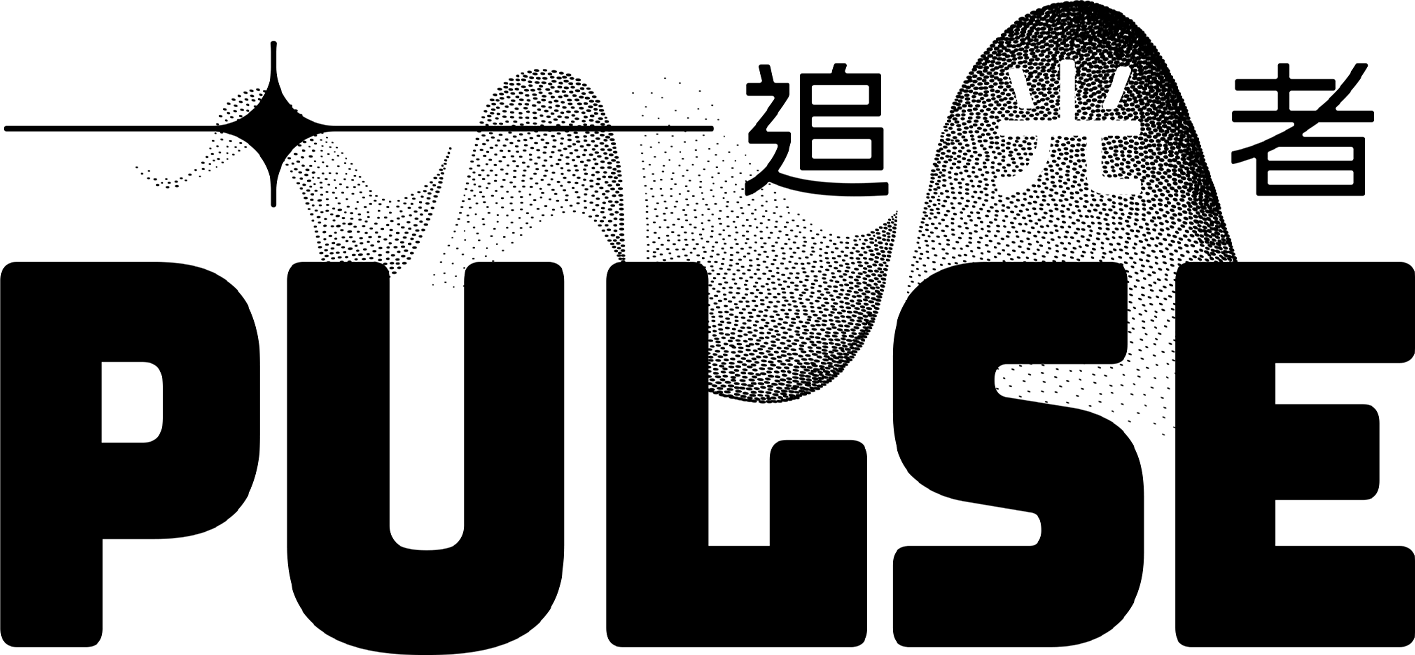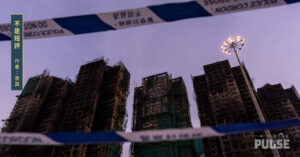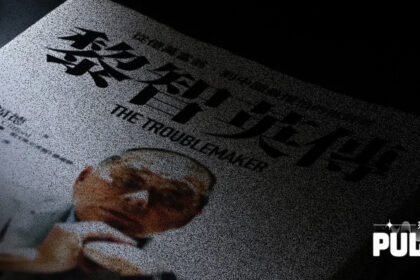經過約四個月的審查,香港導演周冠威的新作《自殺通告》,日前終於接獲香港當局以「不利國家安全」為由發出的禁映通知。周在社媒回應中表示,感到痛苦與不公,並直言整個審查過程荒謬而令人沮喪;同時,他亦表明會繼續拍電影。該片在台灣上映後,卻引發熱烈討論。觀眾的焦點亦很快從精英教育、考試文化與學生自殺問題,轉向一個更令人不安、也更貼近日常的提問:當一個制度口口聲聲說「為你好」,卻無法真正聆聽任何人的痛苦與申訴時,究竟出了甚麼問題?
耐人尋味的是,這種戲內對制度的冷靜反思,最終竟在戲外以現實形式回到導演本人身上,構成一種近乎殘酷的諷刺。《自殺通告》所批判的,並非某個歹角,而是一套在沒有任何人刻意為惡的情況下,仍然造成致命後果的制度。周冠威向來為人忠厚,敘事亦一貫保持克制,電影裡也刻意不塑造任何邪惡反派,或許與現實況存在距離,周卻依然無法避免在戲外被相類似的邏輯所排斥;他甚至連抗辯的機會也沒有,彷彿一切早已因他的過去而被預先標記。這種無法洗脫的「原罪」,是否正來自他曾拍攝《十年》與《時代革命》?
在台灣的影評與社群觀後感中,《自殺通告》是一部以沉穩、壓抑的節奏累積後勁的作品。它不靠煽情處理「學生自殺」這類敏感題材,反而以冷冽而壓抑的氛圍,逼觀眾直視制度如何把人的痛苦轉化為一個「可被管理」的問題。許多影評亦把電影拉回台灣熟悉的升學競爭與考試文化,甚至有人形容,它勾起了「考試 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與「沒有選擇的青春」的集體記憶。也正是在這樣的閱讀脈絡下,當外界得知該片無法在香港上映,並被有關方面以「不利國家安全」為由拒絕時,不少討論開始意識到,電影原本指向制度的提問,已不再只是隱喻,而是以現實形式重現在眼前。
戲內沒有反派的世界,才最令人窒息
《自殺通告》最令人不安之處,在於它幾乎沒有一個可以指責的「壞人」。老師不是冷血之徒,校方也不是邪惡機構;每一個人都在自己的崗位上,依程序、按指引、小心翼翼地避免出事。監控、審查與篩選的存在,亦往往以「為你好」作為理由。然而,正是在這種看似「理性」而安全的運作下,學生的痛苦既未被制度正視,也無從被真正梳解。
這種敘事,正好呼應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Eichmann in Jerusalem》中提出的「平庸的惡」(the banality of evil):惡未必源於個人的惡意,而往往出現在人們在制度之中停止判斷或思考、只求把分內工作完成的時刻。當每個人都只需「跟程序走」、確保自己沒有越界,責任便被層層分散,結果沒有人真正決定要忽視或排斥,但忽視或排斥,甚至迫害卻在制度的正常運作中悄然發生。電影真正質問的,不是「誰做錯了」,而是為何在這樣一個看似理性的系統裡,殘酷的結果仍然會發生?
戲外的禁映,成了最直接的註解
如果說戲內描寫的是制度如何容不下異類,那麼戲外的禁映事件,幾乎成了一個毋須再解讀的現實版本。港府拒絕《自殺通告》上映時,並未公開指出具體問題,而是以高度抽象的「國家安全」作為總括理由,直接終止其公共存在。這種做法本身,正是一種去政治化的語言:它不需要說服任何人,只需要令討論失效或消失。
從斯洛文尼亞文化理論家齊澤克(Slavoj Žižek) 的角度來看,這正好體現了「制度暴力」(objective / systemic violence)的結構性特徵:不必動用可見的衝突,也毋須製造戲劇化的壓迫,只要讓某些事物「不再出現」,制度便能繼續如常運作。在這樣的脈絡下,周冠威在作品被禁後所表現出的態度,才顯得格外耐人尋味。在痛苦與感到不公之中,界線反而變得清晰,藝術工作者毋須再反覆揣測或心存幻想。這種狀態並非解放,而是一種清醒。
投射香港:當「為你好」成為一切答案
這種清醒的「自由感」並不意味着否認現實的壓迫,而是恰恰相反。長期生活在高度不確定的環境中,創作人往往被迫進行無止境的自我審查:哪些能說?哪些最好別碰?界線究竟在哪裡?當禁令以最直接的方式落下,這種模糊反而消失了。
在香港近年文化環境中,這樣的狀態並不陌生。很多時候,壓力並非來自明文禁令,而是來自一種瀰漫的氣氛:你應該知道甚麼不合適。而《自殺通告》的遭遇,正好揭示了這套邏輯的終點:當制度不再嘗試修正你,而是直接排除你,你反而清楚知道自己站在何處,以及出路究竟在何方。
自由非被允許,而是被拒絕後仍站得住
《自殺通告》在台灣被觀看、被討論;在香港卻被禁止、被消音。這種落差,本身已經構成了對香港現況的深刻投射。有影評人指出,《自殺通告》並不是一部控訴誰「做錯了事」的電影,而是一部呈現「每個人都沒有做錯,但事情仍然錯得離譜」的作品。它的批判極其克制,甚至可以說是以中留情。電影沒有要求觀眾憤怒,只是在問制度如何失靈,但這樣的作品最終在香港連被討論的空間都不存在時,戲內的隱喻,已不需要再由觀眾補充。
或許正是這個原因,事件在業界引起的並不只是情緒反應。就連向來立場溫和、深諳行規的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言人田啟文,亦公開呼籲當局交代審查準則,並提出疑問:究竟當局是針對作品,還是針對人?
在一個凡事都以安全、穩定與「為你好」作為理由的治理環境裡,真正的自由感未必僅僅是被允許說話,而是在被拒絕或被排斥後,仍然清楚知道問題來自制度,而不是你自己。這種無悔當初的自我肯定,亦可從漢娜・鄂蘭對「行動」與自由的理解中得到呼應。鄂蘭指出,自由並非免於後果,而是在作出行動之後,仍能對自己的選擇負責,仍然與那個「我」同行於公共世界之中。
因此,周冠威說,他會繼續拍電影,這既不是浪漫的反抗,也不是徹底的釋懷,而是一種看清現實之後的選擇:繼續創作,本身就是拒絕自我消失。就正如有評論人所指,自由不是無畏無懼,而是在痛苦與惶恐之中,仍選擇擇善而行。
事實上,周冠威並非孤例。無論是舞台劇編劇莊梅岩,還是其他近年逐步被排除於主流文化空間之外的香港文化人,他們所面對的,往往並非明確的指控,而是一套無聲的審查與長期的排斥。這種無聲的封殺,雖未至於文革時期「黑五類」的公開定性,卻在實際影響上呈現出相似之處,令文化人藝術工作者難以再以原有的專業身份生活,逐漸成為被排斥者(outcasts)。或許,今天留給香港文化界最誠實的問題不再是「還能否被容納」,而是在被拒絕、被排斥後,是否仍然有人選擇站得住,繼續講、繼續寫、繼續演、繼續唱、繼續拍。
相關新聞
- 2025 年 12 月 01
- 2025 年 12 月 01
- 2025 年 12 月 29
- 2026 年 01 月 16
- 2025 年 11 月 25
- 2025 年 12 月 07
- 2025 年 12 月 08
- 2026 年 02 月 04
- 2026 年 01 月 23
- 2025 年 12 月 18
- 2026 年 01 月 09